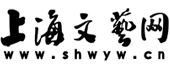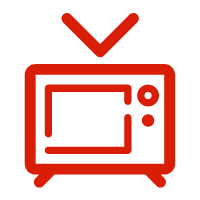今年春节回家,正赶上一个乡邻的葬礼。这位乡邻死于自杀,才刚刚60岁的年纪。按照现在年龄段的划分,他正值中年,生命正处于有穿透力的时候。但是,他却选择了悄然的离开。
当然,乡邻的自杀有着诸多的无奈。听我的父母讲,在他自杀之前的一个月,他被查出肝癌。那时候,他老感觉身体里的某个部位有些不适,起初并未在意,后来,这种不适越来越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就独自上县城的医院检查。医生问他是否有家人同行,他说他一辈子单身,更无子嗣。于是,医生就把实情告诉了他。其实,乡邻骗了医生,他不但有老婆,还有一个儿子,只是老婆和儿子都在广州打工,平时难得回家一次。乡邻就这样一个人独居在山村。
后来我想,他也许不是真的在欺骗医生,而是出于他自己心里的一种下意识。他觉得自己并未享受到家庭应有的天伦之乐,逢年过节,他需要一个人独自对着冷月孤灯,这样的情景,让他觉得自己与一个孤家寡人无异。乡邻在得知自己患上不治之症后,并没有表现得很绝望,他回到村子,依然与左邻右舍相谈甚欢,只是给也觅食在广州的兄弟打了个电话,说明了自己的病情。倒是接到他电话的兄弟表现得惊慌失措,忙不迭地把这一信息转达给了他的老婆和儿子。
尽管这个社会已经让亲情这个词语严重物化,但是,当生离死别真真切切地来到时,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是显示出了它的原始属性。乡邻的老婆儿子,在第一时间赶回了老家。他们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动员他上医院治疗。但是,乡邻似乎早已看淡生死,任老婆儿子如何劝说,就是不为所动。对于乡邻的举动,我无法揣摩个中缘由,但有一点我是明白的——钱花了,最终还是免不得一死。我相信我的乡邻一定知道这个理。他的儿子已经年过30,居然连个女朋友都还没有,他不想让自己行将就木的病躯,再去拖累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而影响儿子的终身大事。尽管他也在心里希望儿子娶妻生子,完成他作为爷爷的人伦之趣。
于是,他乘老婆带着儿子出门办事的一天,自己在家里宰了一只鸡,美美享受了对于久居乡村的他来说,在人间的最后一顿饕餮大餐。然后,悠然地乘鹤西去。事后,觉得蹊跷的老婆儿子,从他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厨房里知道了真相,他在那顿大餐里给自己下了毒,然后宁静地离开了人世。在这位乡邻看来,如此决绝的离世方式,是最为体面的轰然而去。
参加完乡邻的葬礼后,我就在想,在我那已经面目全非的老家山村里,一个生命降临于世,累死累活地苟活了几十年,最后如这位乡邻一样,悲壮地死去。因为卑微,我们短短几十年的人生,注定了无论是活着,抑或是死去,都不可能留下什么。即便是墓碑上镌刻的名字,在岁月的风霜雪雨中,也很快会被寒风吹蚀被雨水洗掉。时间在埋葬我们肉身的同时,也就埋葬了我们的一生,生命就以这样的方式永远的消逝了。
在这些颇为惨烈的事实面前,我总是免不得心怀忧郁——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更让我深感疑惑,我本来就深感孤独的内心里,更加显得脆弱无比。从曾经读过的所有书籍中,我感受到的,生命似乎是可以有多种形式,在泥土之上可以用精神来铭记和延续的,即一个人的活法,也似乎是可以超越肉体意义上的生命的。但是,在我曾经生活近三十年的湘北山村一隅,生命却是如此的千篇一律,活过一辈子死了,被一方棺木包装起来,深埋在自己曾经走过的土地上,一个土堆筑垒起来的没有符号的印记,至多只是一种作为提醒血脉传递的存在标识。当时间过去若干年后,也就再没有谁记住了。
比如我的祖上。按照老家山村的习俗,大年三十的晚上,作为后辈人,是一定要到祖上的坟头去上香点蜡的。当我和我古稀之年的老父,以及我的儿子,来到一片埋葬着我爷爷的坟地时,我们只知道,那里,有我的祖上,至于哪个坟头是我爷爷的爷爷,或者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些隆起的土包,隐藏了这个孕育出一个浩浩荡荡家族生命的秘密。随着我们流浪他乡时日的延伸,这些日渐变小的坟头,在我父亲过世之后,就可能连同一个家族的疼痛,彻底消失在这个空旷村野的角落里,无人再忆起——在时间之上,他们的一生,就这样被失忆般地终结,成为我心底里,无法被别人体会的忧伤。而我总会在心中臆想他们当年活着时的情景,念想他们在泥土之上,悄无声息地来去,他们一生的行程,是否也像我这个后辈人一样,在生存的缝隙间挣扎时,布满了苦乐悲欢?
有一年春节,我和妻子从广州回到老家过年,还没有来得及洗掉旅途上的疲惫,我的爷爷就猝然告别人世,这是我长大知事后第一次亲自送别亲人的肉身。其时,爷爷已经年满88岁。他在生时,经常对我们说,从年龄上讲,人活七十古来稀,而他能活到八十多岁,已经非常知足了。爷爷的一生,颇有些啼笑皆非,作为大字不识一个的山野村夫,解放后被带上一顶地主的大帽。我父母说,爷爷的地主大帽,来于他的笨。临近解放时,他和奶奶真正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勤巴苦做地积攒了些钱财,买下一片田地和几栋房屋,还没有来得及收回成本,人生就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等到摘掉压在他头上,也是压在我们全家人身上的那个精神枷锁被彻底去除的时候,爷爷已经老了,一生过惯了苦日子的他,到了老年,仍然舍不得放下伴随了他一生的锄头镰刀,他在劳作中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多年以后,当我回想起,爷爷在湘北山村那个劲吹着寒冷霜风的冬夜,淡然平静的辞世,恍惚觉得自己为生命的来去匆匆而郁结时,该是多么的幼稚。我不明白,爷爷那种平静地对待死亡的人生的境界和生命的哲学,是不是与那个桎梏了他几十年的精神枷锁有关?我不得而知。
在我的老家山村,像我的爷爷一样,匆匆走过一生的比比皆是。他们活过了,逐渐衰老了,然后就开始为自己平静地准备后事。他们心如止水。还有的因病痛,被折磨得久了,也看到了久病的床前不再有孝子,自己便悄悄地作别尘世。他们的离世,很快就湮没在乡间日常的琐碎里,像一缕薄暮,不留一丝痕迹。
当然,在时代变幻中,如今的山村,也已经不再是往昔的山村了。有很多人虽然生长于泥土,但源于物质的诱惑,他们不再满足于泥土的生活,父辈们苦似黄连般的劳作,让他们千方百计地逃离泥土,来到遥远的异乡,寻觅另外的生活方式。他们的骨子里,没有存留一点故土乡村,他们在异乡拼了命地挣钱。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因为种种原因,客死他乡。最终,他们只能是化成一捧骨灰,被亲人带回曾经被他们遗弃的土地上安葬。故土终究是宽厚且仁慈的,总是能宽容这些飘游于异地它乡的孤魂野鬼。
十年前,我同学的哥哥,本来在山村里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村里的医生,但他不顾老伴和儿媳的劝告,执意来到广州,在一间私人诊所里打工。有一次,老板安排他到一座工业区去为一个病得厉害的工人输液,没想到在过马路时,被一辆飞驰的小车撞飞了。他的儿子媳妇想尽好多办法,想将他的尸骨拉回老家山村,最终未能如愿。回到家里的只能是一个小小的骨灰盒。今年春节回家过年,我从他的坟头边路过,看到本来就不大的坟头,已经被荒草和灌木掩盖,听同学说,他哥死后不久,他在城里工作的儿媳就接走了他们孤独的母亲,从此,几间在当年轰动了乡亲们的老屋,连同同学哥哥的已掩埋于地下的骨灰盒,就留在了山村里。照这样下去,多年以后,他儿孙的儿孙们,要想再回来寻找他的坟头,恐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到那个时候,一个曾经体面地存在于山村的乡土人物,他一生的荣辱与悲欢,就将被时间的尘世所吞噬,而不会有一丁点儿回声。
这些生命中,无论是我的爷爷奶奶,还是那个选择自认为有尊严地离去的乡邻,他们都是这块土地上的平民,他们的一生,庸凡平常。但他们最后都安息泥土之中,最后成为世间的一粒尘土,他们仍然像是一朵盛放过的花,尽管已经凋谢,落入于凡尘,但他们的生命,会一直值得我们去敬畏。
【本文入选2015年中国散文佳作精选集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主编:毕凌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