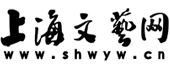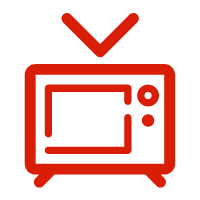在农村人的眼里,曾经,水井与“家”有关。有水井在,就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在,就有兄弟、姐妹与牙牙学语的幼儿在;只要有人喊爷爷、爸爸、哥哥的地方,就有挑水的身影,就有生存的脊梁;有人叫奶奶、母亲、姐姐的家庭,每一缕炊烟,都是温暖,每个角落都充满阳光。 ——题记
一
几天前,住在老家的父亲来电话,说井里的水泵坏了,去换,半人高的野草和密密麻麻的杂树把路堵了,让我赶紧回去。
我安慰了父亲几句,立马赶到老家县城,买上水泵和斧头、锯子,直奔老家。
车出县城,见惯了小城大市水泥林的眼睛,为之一亮。
高远、明澈的蓝天,蓝得只有几缕飘渺的白云;连绵、苍翠的山野,静得恍惚有一两声鸡鸣狗吠;而散落在山野间的一座座红瓦白墙小楼,房上无一丝饮烟、院前没一个人影……
随着车的前行,不知不觉也就想起曾经分布在山崖下、沟壑边、大院旁,一口口形状各异的水井和三三两两挑水的情景,那“叮叮咚咚”的泉水声和井旁妇女的说笑、小孩的嬉闹,便隐约在耳旁,嘴里竟沁出一泓久违的清凉……
队上有水井三口。堰塘湾是简易的平井,艾家碥是七八米深的吊井,我们家则是石门咀的山泉井。
石门咀这井,一个天然的青石坑,僻居于宽宽敞敞的崖洞里。吹风,尘土进不去;下雨,清清澈澈;天旱,不枯不竭。
据爷爷讲,他两三岁那阵就听说,它是口老井。当时去卷洞山挑炭、来鲜渡码头买盐、过大竹采茶、到南充贩猪崽的,走累了渴了饿了,宁愿多坚持一会,也要走到石门咀,才在这崖洞下歇气,待山风吹得人凉幽幽的,几捧山泉水“咕嘟咕嘟”一灌,又继续赶路……
从家里去石门咀挑水,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得经三根田埂过一截水渠,然后是一段下岩的陡坡。落点小雨,坡路就打梭,黄泥巴路则一走一溜,多下几天雨,水渠还长了青苔。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挑水的时候最多, 他那一双又宽又大的赤脚,走滑路最稳。
爷爷挑水,爱用根金黄色的樘木扁担,穿件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衫。由于爷爷高大魁梧,一挑连桶带水120多斤的担子,在他骨骼突起、宽大有力的肩上,便显得没什么分量。爷爷挑水,步子偏大,不急不缓;扯水,水桶从来不着地,前面一只木桶在水面上左右一荡,一侧一搲,满满一桶清清亮亮的水便连挑带提离开了水面,身子顺势一侧,另一只木桶在水里“咕”地一声,两桶水就随着稳健的步子上路了。
那水,不涌不溅,在天光下,扬起美妙的波澜,连桶底木板的颜色、木纹都看得清清楚楚。
爷爷在前面走,我后边跟。爷爷快我快,爷爷慢我慢,爷爷遇上熟人说事,我就停下来。特别是雨天,爷爷那双宽宽大大、薄薄瘦瘦的赤脚,远比别人贴得紧,5根细长的脚趾竟像5把爪子,每走一步,脚一接触地面,脚趾就在一溜一滑的泥路上,抓陷出5个深深的趾印。这时,我就踩爷爷的脚印。“踩脚印”特灵,即使偶尔踩得不稳,不时一滑,另一只小脚赶紧一站,也能稳稳刹住。
印象最深,还是晴天挑水。我们爱跑在爷爷的前面,常常是沿路小跑一阵,见爷爷被甩得远远的了,才停下来在路边捉蚂蚱,或爬到树上去抓知了,等到爷爷那穿着长衫的身影近了,我们又一阵猛跑,身影一闪,就钻进了稻田。一会出来,手里竟举着两条小鱼……
爷爷挑水,两只桶一前一后,不摇不晃,水不跳不溢。换肩,只轻轻一磨,扁担就到了另一只肩。走到水缸前,肩上的两只桶后低前高,前桶只轻轻一靠缸沿,一倾,满满一桶水如液如玉一泻而下;身子一侧,前面的空桶在后,另一只桶与缸沿一靠,水冲击着水,“轰隆”一声,似乎在提醒挑水的人,一担水还远远不够。
如此重复数次,三四担水挑完,爷爷才把长衫下摆一搂,在小板凳上坐下,不快不慢卷上一支叶子烟,往铜烟斗里一栽,“啪”的一声点上,“哧哧哧”地吸起来……
当问及爷爷挑水,为啥没摔过跟头时,爷爷说,挑水这活就像写字有转弯抹角,读书要抠字眼。需细心的,你加倍小心;要八十斤力的,你使上一百斤的劲。天下就没有做不好的事……
二
随着爷爷年岁高,父亲干的又是吃百家饭的石匠活,很多时候,家家户户都点上灯了,父亲才能回家。桃水的活,逐渐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
早晨,父亲要桃了水出门,母亲会一下夺过扁担,说打石头是重活,安全要紧。常常是父亲出门,母亲也挑着空桶“叽尔嘎尔”出去了。一会,两声“哗啦!哗啦!!”的倒水声传来,一般是母亲挑的第一担水;过一会,又听到“哗——!哗——!!”是第二担;再听到“轰——!轰——隆!!”多半是第三担……
邻居听到倒水声,才陆陆续续挑着空桶出门。于是,一个个院子通向水井的路上,便会有三三两两挑着一担担空桶出门,然后,又挑着一担担清清澈澈的井水回家。不到一刻钟,从井台蜿蜒到一个个院子的石板路,就像一条条“水龙”。
人家才把水挑回,母亲已喂罢牲口、扫了地坝,把头也梳毕了。只听得,出工哨骤然响起,“驱——驱驱驱驱!”远远地就有人高喊:“全劳动(壮年男人),在廖家塝犁田抓边;半劳动(妇女),在艾家碥挖洋芋;老年人,在观音溪河边垮胡豆角哟……”
邻居们还在屋里屋外找农具、慌慌张张关门,母亲已扛着锄头下了地,往往还是前一二名。
若是连续几天熬夜抢收抢栽,或白天忙队上的活,晚上还突击自留地,一到煮夜饭才发现缸里是干的,母亲二话不说,会连忙挑回一担水,就给我们煮饭。
待一家大小饭一吃,借着热锅热灶,洗脚水也热乎乎的了。母亲又提醒:“洗到后头的,是龌龊水哟!”
有时父亲在石厂办大山、打大锤,或抬大号石头上船,回来瘫软在床上不想洗脚,母亲会多烧两把火,舀上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脚水,朝父亲喊:“看你那双臭爪爪,水舀起了!”
如果是我们不想洗脚,装着没听见,母亲准会警告:“一个儿娃子,手脚伸出来黑得像熊掌,今后哪个女娃儿嫁给你?”
在农村,人离不开水,鸡鸭牛羊猪猫狗要水,田间地头的庄稼渴了饿了要喝水。特别是秋夏两季,年年都会连续干旱十多天,甚至一两个月,一眼望去树萎草干,村里村外水塘龟裂、十井八枯,别说煮饭淘菜,连牲畜的饮水也得到大河或水库里去挑。
从我们家去河里挑水,虽只有一里多路,但挑一担水要上五六百米的陡峭山路,就是壮劳力连续三四趟,也登得脚软。可是,一家大小六七人、外加两三头猪要吃要喝,少了水能行?去挑,在那个听哨声出工、天不黑不收工、靠工分分粮的年月,谁有那么多时间?很多时候,特别是干旱的夏天,从渠江边到岸上院子的山路上,常常天不亮就看到提着马灯挑着空桶下河、黑灯瞎火了还打着火把挑着水回家的身影。
于是,一口口近在咫尺的水井,不知从啥时开始,村里就有了等水的现象。一到夏天秋天,在农村沟坎边院子旁的井台边,几十担水桶逶逶迤迤排成长龙的壮观景象随处可见……
村里有一家人,外号叫“武欺头”(欺头,四川指占小便宜)。年年等水都要插几回队,或趁人不注意多舀一担,常常是今天和张家吵,隔几日又跟李家骂。记得有年,“武欺头”未过门的儿媳家突然来了四五人,他家正想烧火做饭,才发现缸里没水。想到河边去挑,来去得半小时;在院子里借水,谁都不肯给。
母亲知道后,立即把我们家刚舀上的一担水,让他挑了回去。第二年夏旱,那人的母亲去世,他一下提来三四担桶霸着舀,曾经与他吵过架的几家死活不依,还是母亲出面相劝,大家才放他一马。
从那以后,那家才一改对谁都“狠”的老毛病,开始对我们家“仁慈”点。
挑水,母亲也有意外摔坏水桶的时候。
六十年代末的一个雨天,父亲在公社修语录牌,爷爷去河边抬石头上载了,生了幺弟刚满月的母亲,身体虚弱。母亲在队上栽苕回来,正要煮饭,见缸里水到底了,强撑着身子去挑水。当时,我们家用的仍然是有弯弯横梁、梁上系着一组棕绳、仅空桶就有20多斤的木水桶。要强的母亲,以为她平时经常挑水,最多咬咬牙就回来了。哪知,戴上斗笠、光着脚丫的母亲,在风雨飘摇中,拖着身子挑罢第二担,在挑第三担时,脚下的硬头滑泥巴一溜,一跟头下去把水桶给摔漏了。两只水桶在她一路小跑中,小孩撒尿般边撒边喷。到了家里,一个桶只剩了少半,一个桶几乎漏完。
一贯脾气暴躁的父亲回来,见母亲手臂摔破了,立马拧开酒瓶倒了点白酒先给伤口消毒,再从箱子里取出表哥从部队寄来的云南白药撒在上面,还找出一绺新白布给包扎。
从这天起,连续一个多月,父亲利用中午、傍晚,和爷爷抬来一些长短不一的条石,把原来的土梯子砌成石梯,每天还顺便从石厂背回两张卖不出去的异形青石板,镶铺在去水井的路上。当石板路铺延到一家与父母有旧冤的田埂上时,那家死活不许,说是铺上的石板万一滑到他田里划伤了牛脚,要我们家负责。
谁都心知肚明,原因是一旦我们铺上石板,等于阻绝了他家“一年削一点人家地边田埂”的蚕食行为,但母亲还是没准父亲铺,她说,锅边上的几颗饭吃不饱!与其和这种人争强好胜,不如把精力放在挣家业、育子女上;仓里有粮食,子女有本事,人家自然就会高看你几分……
哪知不久,母亲脖颈出现隐痛、触摸到有疙瘩状,去医院一查,已到淋巴结核中晚期。几兄妹接她到重庆、达州治疗,待药一开,她总是说,家里喂着猪牛还有鸡鸭,父亲一人忙不过来,执意要回去。回到家,父亲不让挑水,她说挑水煮饭是一套活路,依然天天挑水。后来,父亲看不下去,强行阻止她摸扁担,才勉强作罢,但遇上缸里水不多,母亲仍会悄悄地去挑上一担两担。
到第二年,癌细胞扩散到全身,痛得母亲天天晚上起来走,她也没喊过一声“痛”。见母亲脸形变了,父亲也憔悴了,一下变得沉默寡言。
渐渐地,生产队便出现变化。过去几十年在这口井挑水的是十三家、吃水的有七八十人;后来只有七八家、二三十人;再往后,3口井只有两三家、十余人在家;到母亲去世,只剩我们一家、父亲一人了……
三
作为农村家庭的长子,父亲在我眼里,支撑和丰盈他形象的,还是与“挑水”有关。
记得是我十二岁那年,母亲见外边大雪纷飞,让父亲去挑几担水,下午要推些豆腐,给过年熏些豆腐干,以备正月待客下酒。哪知,父亲一去两三个小时不回。母亲把豆子择净淘洗几遍,一解腰上的花围裙,出去一小会就把父亲逮了回来。
一家人见父亲回来了都不吭声,爷爷指指父亲挑回的水问,你这水在哪里挑的?父亲咕噜了一句,石门咀。爷爷眼睛一抡,我以为是外国买的呢!见父亲没了言语,爷爷又说,干干净净的一眼泉水,好好的一口井,你是想把源头搅浑、把水井弄废,有点空,清清净净休息一下、陪陪孩子不好?十赌九上瘾!一家之主没个正像,小心前头作揖后头勾腰,好好几棵苗子都让你毁了哦……
从那以后,就恍惚觉得,我和兄弟妹妹们就是父亲肩上的两只水桶,任何一只摔烂了,一家人都会坍塌。从此,父亲也像变了个人。出门做手艺,再不摸扑克麻将;在队上出工,即便是歇气,别人喊“整两把”,他也是婉言拒绝,只和几个德高望重的人摆摆龙门阵清耍一会;遇上下雨天,就编背篼箢箕或收拾农具,把一水缸挑得满满的;要是大年初一,父亲会天不亮第一个去挑水,见水缸差一两担满了,才让我们去接着挑。说是新年头个日子,挑第一担二担水是金水银水,是财运;挑第三担四担是墨水,子女读得书;我们接着挑,才会越读成绩越好,代代出秀才;正月初二这天,给外公外婆、舅父舅母家拜年,父亲一支烟一抽,就得帮外公外婆桃几担水,俗称“贵婿添财”;拜了年,回到家,换上旧衣服,一拿扁担,挑上水桶,说开了春,活路出来了,要做秧田撒谷子呢!一会,就挑上明晃晃一缸水,两三天不挑也够用……
父亲桃水,与别人不同。也许是父亲个头比爷爷稍小的原因,他总是挺胸抬头,似乎没注意过脚下,可脚步特快,一手搭在扁担上,一手则前后甩得活泛好看,两只水桶也欢快地跟着闪悠悠的扁担上下起伏、一颠一颠前行,桶里的水便扬起好看的波澜,却没一滴水溅到桶外。几担水桃完,若家里要推苕粉、淘干咸菜或有客人来,母亲则会提醒:“蒋吉树啊,明天用水有点大哟!”
父亲二话不说,会多桃三四担,装八担水的石缸,几乎盛得满满当当,有时地上还搁着满满一桃……
要是酷暑天干、十天半月不下雨,地里的庄稼萎靡不振,母亲睡下会突然想起似的,轻声提醒父亲:“下午我打米回来,看到沙咀上那红苕叶子都黄了;估计麻地弯那几窝南瓜,也快点得燃火了吧!”
第二天,父亲准会提前半个时辰起床,不声不响从井里桃些水倒进粪凼,然后兑出淡淡的粪水去给庄稼解渴,一忙就是三四天;即便是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睛的晌午,再从地边过,都能看到那泥巴有些湿润,苕尖、南瓜藤都比邻家的头抬得高,还多了几分绿意;挖苕时,人家的苕手指般细小,我们的又粗又大又多摆一地……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身上有股使不完的劲,那肩永远压不垮,一双腿脚,似乎天生就迈得飞快不知疲倦……
恍惚有水井在,就有父亲、母亲在,就有兄弟、姐妹与牙牙学语的幼儿在;只要有人喊爸爸、哥哥的地方,就有挑水的身影,就有生存的脊梁;有人叫母亲、姐姐的家庭,就有炊烟,每个角落都是阳光,每件家什都有温暖。
在我眼里,水井总是与农民的命运有关。水井边的笑声多,热闹,农村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挑水的人络绎不绝,繁忙,农村的青壮年、大娃细崽便多,日子就有盼头……
“嘀嘀!”一声喇叭响,才发现车停在了老家的青石地坝上。父亲见我提着新崭崭的水泵下来,竟兴奋得像个小孩,一边过来帮我提装有电线、插头之类的袋子,一边说,见我要回来,早上顺着公路,专门去堰塘湾挑了两个半担水回来煮饭。饭,是我最喜欢的红苕干饭;菜,是我早就念叨了无数回的炒青菜;咸菜,是我一端碗就要的胡豆瓣臜生姜。
这才发现,父亲一下苍老了。两只眼睛,浑浑浊浊;眼角,爬满鱼尾纹;原本的发须只有零星几根白丝,竟也“发须皆白”。
父亲见我想安慰他,连忙提着袋子前头走了,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没啥没啥,只是感冒几天。
我知道,只要问到委屈、遭遇一类的事,父亲都会立马转移话题,再多的心事,都会藏在肚子里。不便再问,我就去解燃眉之急——换泵。
从家里找来套旧衣服套上,沿着通往水井的路才走30余米,齐人高的茅草和密密麻麻的野刺槐就挡住了去路,连猫狗都不敢钻进野刺丛中。
我侧着身迂回前行,遇上挤不过身的地方,砍掉新长上来的刺槐;一时半会砍不掉的,绕着走。约十多分钟来到水井边,井台上已是绿油油的一层苔藓,满满的一井清水,清得连过去等水时下去舀水的石梯和人影,也一清二楚……
把旧泵提上来,换上新水泵,让父亲那边上闸,一会,父亲便激动地大喊:“对了对了,水来了!”
四
水缸刚抽满,几个七十多岁来铲草修路的邻居也到了。
一见他们个个佝偻着腰背、一双双手十分粗糙干瘦和皱得像老苦瓜皮的一张张脸颊,还有那眸子里曾经熟悉的亲和,我想给点钱让他们回去,不雇他们了。想了想,又无法让他们回得有尊严,只好一人给一包烟,请他们先喝一会茶。
几个老人默默地抽着烟。透过烟雾,面对一张张沟沟壑壑的皱脸,一股莫名的情绪蔓延开来。由他们的苍老、弱不禁风及父亲的衰老,一下意识到乡村更甚的衰败。
此时,正值“秋后十天满田黄”,原本巴蜀农村,几千年不变的耕种景象竟悄然遁尽。沟里坝上和梯田,无边无际的稻黄,已变成茂盛的野草和虬劲的杂树;山上山下,层层叠叠曾栽种着数十万亩绿油油的苕地,没一道梁没一面坡没被荒弃,只有大路边偶尔种了巴掌大一小块的红苕或玉米之类的农作物,在告诉世人,这里还住着一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那是他们想像过去一样每年豌豆、胡豆、小麦、稻谷出来了可以尝尝新,在怀念曾经的岁月;村里村外,以前一个个堰塘水库滴水不漏、一条条水渠不残不缺,眼下只要从国道一拐进村道,两边烂堰断渠缺埂随处可见;过去一座座房上静静地袅绕着饮烟和檐下挂满玉米棒子、红辣椒的情景,也成昨日记忆;不时从沟底下或山寨上传来一声鸡鸣、几声狗叫便引来的此起彼伏,此时已听不到一点声音,很难见一个人影……
不知不觉,来到一座三间土墙茅草房前,这是我儿时的偶像“三高”家。当年,他文化高,是村里的老三届;理想高,立志要当干部;但成份高,属富农。便落下“三高”这一雅号。
由于父母对我们从小灌输“读书是农村娃儿的唯一出路”,比我大整整十岁的“三高”,自然成了我的“大朋友”。后来,因家庭成份,“三高”回家务农,再经东奔西窜,终于进了大队企业,干着有工分还有些补助金的活;再后来,从会计、主任到入党当村书记。
“三高”一直都羡慕城市生活。时逢新农村建设,县里在棕滩镇河边修了一群小别墅,他以为天上掉馅饼了,倾囊拿出10多万元积蓄,买了一套。哪知,上面不给办房产证,气得他差点吐血。更糟糕的是,包产田地在十里外的老家,每天耕种,早上租摩托去晚上再回,仅车费就要26元,收几颗粮食还不够车费;害得老伴天不亮就起来煮饭、他在田里坡上喝口开水都不方便不说,中午还得吃带去的冷饭,几年下来,人都吃起了胃病;最要命的是吃喝拉撒在一方,田地在另一方,要把上好的人牲粪便送到地里,再将苕腾、南瓜叶、胡豆叶一类的猪草运回去喂猪,豆腐都成了肉价钱。田地使用两年纯化肥,硬得像铁板一块,别说粮食有剩余,即便养活老两口都成困难。回老家住吧,舍不得镇上舒适的环境;继续留在镇上吧,田地得荒废,吃的从哪里来……
从表面看,“三高”老家的房子不垮不漏、地坝仍然干干净净,却再也见不到过去房前屋后鸡鸭成群的气息,猪圈牛栏空空荡荡,粪坑茅厕干起灰。
几次回老家,家家景况相同,走遍全村上下,一片死寂……
和几位老人喝了一小会茶,我拿上铁锯就一起干起活来。他们在后面铲杂草、砍乱枝,我在前面锯挡着道的刺槐,一路上的每一块石板、每一个缺口、每一步石梯,即便闭上眼,是拐弯还是直走,高低宽窄,我都熟悉得像自己的指头一样。
不知不觉,铲到当年不让铺石板的那家青瓦石头墙院子前。只见他家一个转角连着的三间正房,一扇扇紧闭的门窗,已蚀烂霉朽,落满了尘沙和雀鸟粪便;靠卧室的一扇窗半开半关着,窗口织满了蜘蛛网,估计多半是主人忘了关,或插销朽烂所致;房后的山梁上,埋着和我母亲结怨数十载、闹架打架无数次的女主人,坟旁的新坟埋着她的长子;房前栽着的李子树、桃子树、橙子树,泛着幽幽的绿,一个个硕大、黄灿灿的橙子已无人采摘,掉了一地……
再往前,是条宽大的岔路,当年邻近两个队谁家有红白喜事井水不够,或新媳妇进门,要用山泉煮饭下面需到石门咀挑水,这里是必经之路。邻里碰头,都要打个招呼;表哥表嫂、弟弟堂嫂相遇,总少不了几句荤话;放学的歌声、儿童的嬉笑与耕田犁地的吆喝,经常在附近混响……
记得几兄妹都成了家那阵,农村还没有多大变化。父亲、母亲互相陪伴,双双清早一起下地、晚上一同归家、赶场天两个穿得书书气气、兜里揣着我们给的零花,日子过得从未有过的温馨,村里人见人羡。
母亲去世后,妹妹接父亲去一起住,父亲说农村清静;弟弟给他把别墅买起,他说城里的洋房晃眼睛;我说请个人照料,父亲摇摇头说,别出馊主意。
父亲放不下母亲,放不下这个家,放不下荒芜的乡村。
怎奈,岁月沧桑。一个以一双瘦肩桃水、两只磨起老茧的手支撑着一家七八口人体体面面生活的铮铮汉子,到如今,面对野草封死了路,却被折磨得没了人形;几条宽宽大大的路,和沟坝的田野、满山的坡地,野草竟如瘟疫疯长。
生产队没有了,村庄没有了;昔日的三千多人,只有三五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守望着天空。
冥冥中,这几个耄耄老人仿佛是当年患病的母亲在等待生命的终结,又像树与根在等着“叶落”……
我想到了邻村,有人病死在床上几天才被邻居发现;还有一家儿女忙于事务,突然想起老人,一个电话打回没人接,到老家才发现老人倒在青菜地里,躯体已腐烂数月;还想到每次回老家都会遇到几起出殡,或远或近传来高吭嘹亮的哀乐……
忽地,心头竟闪过一幕预兆:
有一天,父亲像这水泵停止了“转动”;村里村外,通往一口口水井的路,也会被荒草杂树封死的;那时,一口口老井,便是一只只明亮的眼睛;一处处源源不断养育了几十代几百代人的清流,都会剩下一个失去主人的水泵陪伴它,告诉N年后的拓荒者,这个荒芜人烟的地方,曾有过昌盛的农耕和温馨的炊烟……
2018年8月26日于达州敬字斋
蒋兴强/文
(首发《连云港文学》杂志,被《达州晚报》等多家报刊全文转载)
注释:
全劳动:又称全劳力。指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农村集体生产时,挑、抬、耕田耙地一类重体力活,一般是壮年男人干,计工10分;而稍轻松一点的活,则由妇女、老弱一类人干,计工8分、7分、6分不等,称“半劳动”,也代指妇女。
欺头:四川指占小便宜。
作者简介:蒋兴强,笔名江夫、江帆,作家,达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攻中篇小说、散文,在《中国作家》《四川文学》《延安文学》《滇池》《青年作家》《散文选刊》《诗刊》和《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重庆晚报》等近百家刊物发表作品400余万字,多次入选权威选刊和优秀作品年选。冰心散文奖、第二届中国散文特等奖得主,达州市“抒写巴山”全国征文中篇小说一等(最高)奖获得者。出版散文精选集《远去的野渡》、中篇小说精选集《丢失》、40万言长篇小说《楚良》。
责任编辑:杨博 沈彤
新闻热线:021-6131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