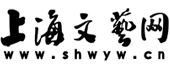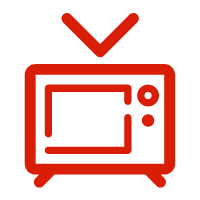1972年10月,美国人威廉·夏利夫和他的日裔妻子青柳昭子与植物学研究者、营养学家、历史学家,以及传统豆腐工匠和烹饪大师一起,开始了他们的黄豆食品研究——在他们的眼中,那是“不可思议的健康食物”。1976年,威廉夫妇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法耶市成立了黄豆食品中心,建立起全世界最庞大的黄豆食品资料库;他们的著作《豆腐之书》将豆腐及其文化推广至欧洲,30年来被欧洲热衷于豆腐食品的人当作圣经。
这本书的台湾中译本上有这样一句话:“世上最终极的美食,就是豆腐那朴实的风味与芬芳!”
每天吃着豆腐却浑浑噩噩的我有个感觉:对豆腐如此高超的评价,定是出自一双能够跳出汉文化圈、“旁观者清”的眼睛,或是来自一颗潜入汉文化内核,体尝了中华食文化深味的心灵。在那评价后面,台湾的出版人接着说,我们是“豆腐民族”的子民
好吧,作为“豆腐民族”中的一员,我对雪白的豆腐青眼有加。我向一位学者请教:世界上很多国家种植大豆,为什么偏偏中国人用大豆做成了豆腐?答曰:中国是大豆的故乡,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栽培大豆的民族。再问:这其中有逻辑必然吗?答曰:豆腐的发明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
有着朴实的风味与芬芳、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气息——豆腐,只是出自一次偶然?我不信。
大豆篇:豆腐的父亲母亲
豆腐是用大豆制成的,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样吃大豆的,大豆又是怎么样养育了中国人?解读豆腐的这位“长辈”的身世经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明晰豆腐出世的背景。
“采大豆呀采大豆,用筐用筥里面盛。诸侯君子来朝见,王用什么将他赠?”这两句诗歌译自《诗经·小雅·采菽》,讲的是三千年前诸侯来朝,周王给予赏赐的事。诗歌作者、某位士大夫是用采大豆的场面来烘托欢快热烈的气氛。菽,就是大豆(菽,音shū,大豆的英语soy就源自此音)。《诗经·小雅·小宛》还有“中原有菽,小民采之”的句子,这类提到“菽”的歌辞在《诗经》中有许多处。这说明,在周朝到春秋时期,大豆已经是比较常见的作物。
不只常见,还很重要。《周礼》中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之说;一般认为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也说“五谷为养”。东汉的经学大师郑玄注释曰,这“五谷”乃麻、黍(黄米)、稷(粟)、麦、菽也。可见两千多年前,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之初,大豆已经开始为中国食文化的孕育提供营养了。
“大豆是唯一一种国际公认的中国原产的谷物。”中国农业大学李里特教授告诉我,“粟、麦等虽同样位列五谷,是古代中国人很重要的粮食作物,但它们的原产地在国际上都有争议。”这意味着在数千年前,只有华夏大地上的先民们能够种大豆、吃大豆,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根本没福享受,大豆在中国一枝独秀。
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大豆的蛋白质含量约占40%,比任何一种谷物的蛋白质含量都高得多,单按蛋白质含量计,1公斤大豆相当于2公斤牛肉,这些毫不起眼的豆粒竟有“田中之肉”、“绿色的牛乳”等美誉。而且大豆蛋白质含18种氨基酸,其中就有8种是人体必需、且不能自我生成的,“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有关机构确认,大豆蛋白可称为最理想的、营养价值最高的蛋白。”李教授说。
当然,这些都是古老的中国先民们所不得知晓的。他们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观察野生大豆,并通过长期的定向选择、改良育种,培育成可大面积种植、收获的栽培大豆,只是为了谋生。国内外研究者们发现,北至黑龙江以北,南至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的广阔地域上,东北、华北、江南等地都有证据可被认定为是大豆起源的中心。1959年,山西省侯马县发现了距今2300多年的战国时期的大豆;上世纪80年代,陕西省扶风县案板遗址又出土了距今4620年的钙化豆类颗粒。究竟哪个地域的中国人最先栽培了大豆,至今仍没有定论,也有学者认为,大豆在中国的起源地是“遍地开花”、多中心的。这些发掘、追究或许有益于大豆的基因研究,但对古老的中国人来说谁是第一无关紧要,重要的事情是,商代人把菽、粟、黍等作物写进 “卜辞”;在甲骨文中可以辨别出黍、稷、麦、菽等“是当时人民依以为生的作物”。
“先秦时期,小米和大豆是人们主要的粮食。”农业考古学家陈文华说,“战国时期遗留下的许多文献中记载了这样的现象:粟菽不足,则民将暴乱。”《墨子·尚书贤》则说:“菽粟多而民足乎食。”可见,战国时大豆已经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两大基本口粮之一。《战国策》中还有记载:“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饭,指“粒食”,古老的中国人最初是把麦子、大豆等直接煮成食物,这种煮蒸而成的颗粒状食物与西方人烧烤制成的面包等“粉食”相对,是东方人特有的,墨子就曾说过“今天下之国,粒食之民”;藿,是大豆的叶子。陈文华先生告诉我,这个时期,把大豆发芽做成的豆芽菜已经出现了,普通百姓的饭桌上,除了煮熟的粒食豆饭,还有用大豆叶和大豆芽做的菜羹。
这里有个称呼的改变引起我注意:《战国策》把“菽”称作“豆”了。事实上,“豆”字的出现最初是指一种青铜食器、礼器,就像它的甲骨文、象形文字“” ,先民们用它盛放食物、蔬菜和酱,可为什么黍、稷没有因为盛它的食器而转换名称,“豆”却单单被用来借指菽?《中国饮食文化史》的作者、文化史家王学泰先生给了我一个有趣的推测: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用豆、笾这样的高脚食器来盛零食,除了瓜果,粟、米恐怕难入其中,而菽粒倒是可以煮来拌些味料,放进搁置在跪坐的膝旁的“豆”中,闲来当作零食来嚼。这么亲切的吃法,自然值得人们放弃它严肃的名字,换个昵称喽!
据史料记载:西周以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豆的栽培规模迅速扩大。中国最早的农学著作、西汉农学家汜胜之撰写的《汜胜之书》有记载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后世学者按这标准算了一下,当时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要把1/4的土地用于种大豆。直到魏晋至隋唐时期,在灾害年份,豆类作物受损也还是地方向朝廷上报灾情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农业科技史稿》总结了一下大豆成为中原人民主粮的原因:大豆果实能当粮食、叶子能作蔬菜,比较实用;大豆植株的根瘤具有固氮的作用,可以补养土地的肥力,种植大豆参与其他谷物的轮作,有利于在谷物连种的情况下用地与养地相结合;而且大豆比较耐旱,具有一定的救荒作用。西晋时候,有人向晋惠帝司马衷报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司马衷答曰:“何不食肉糜?”此话令这位以昏庸、痴愚著称的皇帝名垂史册,倘若司马皇帝给一句“何不食豆糜?”恐怕更靠谱一些。
事实上,即使风调雨顺、年景太平,中原的老百姓也不可能天天食肉糜、喝肉粥的。在战国、秦、汉的数百年间,中原地区已经基本形成了以谷物素食为主的农耕食文化。从事畜牧的部族,或者被农耕部族同化,或者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带,一条长城,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类型,隔出了明显的空间隔离和文化分野。在长城以南,农业生产力随着各种精细农具的出现和农耕技术的进步得以不断提高;在人口压力的驱动下,大片森林被砍伐、草地被开垦为农田,狩猎、畜牧的从业机会进一步降低,中原地区居民的饮食生活,也更加仰赖于人工栽培和饲养,越来越倚重于黍、粟、麦、麻、稻、菽等少数几种谷物。而且,从事农耕生产的定居人口,远比奔走在马背上、过游牧生活的人群更有利于统治者巩固中央集权统治。中原地区几乎成了农耕者独占的天下。“农耕食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粮食谷物搭配蔬菜为主。” 李里特教授说,“中国人吃饭一向饭、菜分离,自由搭配。饭是谷物,菜呢,草字头,是以素菜为主。”肉糜?它只能出现在贵族的日常食谱上,对于普通人家,肉食只能是偶尔的调剂。换一个角度说,中国老百姓、生活在地球上农耕文化圈中心的居民们,他们肉食很少,以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大豆为主食,恰巧可以弥补蛋白质摄入不足的境况。
可惜,把大豆粒煮来当饭吃,恐怕并不好吃,它只是清贫人家的主要膳食,甚至被看作是下等食物。当时形容谁家境贫寒,就称其食豆饭好了。汉代一篇记录奴婢契约和劳动情况的文章《僮约》,描述了雇工“仅可食豆饭和饮水”的条款,一名雇工当得知这些内容以及“其他侮辱性的言行”将被写入雇佣他的协约中,竟哭了。不过,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发现,古代中国人对大豆还有另一种吃法,即:将大豆放入水中长时间煮沸,做成可口的豆粥。他认为“这是当时经常处理和食用大豆的方法”。比如《后汉书》等史料就记载了东汉开国名将冯异,在一场艰苦的战役中军队饥寒交迫时,是怎样为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熬豆粥的;《晋书》中也记录了富豪石崇对熬制豆粥很费时的评价;南北朝时的节令风物笔记《荆楚岁时记》还记载,当时楚地每年正月十五制作豆粥是新年祭祀典礼的一部分。这些大概算是贵族阶层食用大豆的情况吧。
将大豆食用方法的“阶级性差别”拉近的,当属一种叫作石磨的工具,它的推广,令中原人民食用的谷物可以加工成粒食以外的更多食品样式,大豆的吃法有了大突破。
现在所知最早的石磨出自东周,汉唐文献则把磨叫作“硙”,《说文》还说“公输班作硙”,可见磨的出现对于粮食加工意义有多么重要,它需要工艺精巧之匠人来发明创造呢。到了东汉,石磨制作已经有了大的发展,磨出的粮食颗粒越来越精细,特别适合加工小麦和大豆。这时,“饼”出现了,这是中原人民主食发展的一个阶梯,从此,饼开始与粥、饭平分秋色,胡饼(类似今日烧饼或烙饼)、蒸饼(类似今日馒头包子)、汤饼(似今日面条或水饺)出现在百姓的饭桌上。另一方面,汉代已经发明了一种专门用来磨浆的石磨。考古人员在满城汉墓发现了这种石磨,它由木架支撑,漏斗下放置容器可以收纳米浆或豆浆。西汉著作《盐铁论》中列举了西汉前期出现于食肆中的20款时尚食品,其中有一种叫作“豆饧”,众多研究者认为,那就是甜豆浆或者豆腐脑——看来,我们与两千年前的汉代人有相同的习惯,喝甜豆浆、吃豆腐脑,至今仍是时尚的健康早餐哟。
豆腐篇:豆腐的出生证
在游牧民族驰骋于草原大漠奔抢口粮、海洋文明的缔造者们忙于海上贸易的时候,华夏民族的古老居民们正固守在黄河中下游的土地上,将智慧、工巧用于农耕技术的改良、谷物食品的改善,被素食养育了的他们在这种农耕食文化的必然发展脉络中,用大豆制成了豆腐——历史哪有纯粹的偶然?
后来,人们从豆浆久放变质凝结这一现象中得到启发,终于用原始的自淀法创制了最早的豆腐。”学者安忠义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这种由着豆浆自我生成豆腐的办法毕竟太原始,又不能在短时间内做出大量的豆腐,所以,另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人们在给豆浆中加入食盐或卤汁调味时,无意中发现了盐卤对于制作豆腐的巧妙作用—正是那句著名的歇后语:“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千百年来中国人做豆腐最常用的手艺就是用卤水点制豆腐,卤,就是快速把豆浆制成豆腐的凝结剂。
卤是个象形字,原指盐罐或盐池中有盐,后来字义演变成“天然生成的盐”,最后发展为制盐时残留在盐池中的汁液,或者盐碱溶化后的液体。卤的主要成份是氯化镁、硫酸钙等,味苦、有毒。现代歌剧《白毛女》中有个情节是杨白劳喝卤水自杀而死,其实抢救这样的中毒者,可以立即为其喂灌大量豆浆,让胃中的盐卤与豆浆作用生成豆腐,从而解除盐卤的毒性。这当然是个神奇的化学变化,卤水中的氯化镁在与豆浆中的蛋白质发生作用后,结果是蛋白质溶液凝结成凝胶。豆腐就是这种蛋白质凝胶。
化学家袁翰青先生认为,最先制作出豆腐的应该是农民,是他们在长期煮豆磨浆的实践中,得到了这种远比大豆饭美味可口的食品。也有学者不同意此观点,中国古代的许多素菜珍馐都是由僧侣道士、逸人野老和养生家们发明创造的,豆腐的发明为什么不能归功于他们?
南宋的儒学大师朱熹有次写了首咏豆腐诗:“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王术,安坐获泉布。”他自注道:“世传豆腐乃淮南王术。”后两句诗是说,如果他早些掌握淮南王传下来的做豆腐秘方,也能日进斗金,坐发大财了。这位大理学家潜意识里是否有对发财的渴望后世人没有追究,他说豆腐乃淮南王首创,倒是一传再传,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又引用这种说法,于是几成定论。
淮南王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堂叔,是西汉知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与众门客著成集道、阴阳、墨、法和儒家思想的论文集《淮南子》一书。此人尤好道家方术,据传他曾将鸡蛋去汁,以艾草燃烧取热气,使蛋壳浮升。不知这是不是道家升天的试验,反正刘安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实践者”。在刘安招募的门客中,苏非、李尚、左吴、陈由、伍被、毛周、雷被和晋昌这8个人最具才华,号称是淮南王府上的“八公”。他们与刘安在淮南国都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东北面的山上论道、炼丹、寻求长生不老术,此山后来得名“八公山”。当地文献记载了这样的传说:刘安和这八公用豆浆培育丹苗,用后就倾倒在山上,一部分豆浆贮存在坑洼处,因为泥层中含有石膏或盐碱,豆浆便凝结成柔软固体。人们取来煮食, 味道鲜美,因而名之为豆腐。
《淮南子》一书有专部撰写道家炼丹的黄白之术,不过刘安如何用豆浆培育丹苗,没有记载。有关炼丹的一些资料上说,炼丹家为了不使所炼丹药飞散,保持精华,并减少丹药在烧炼时对人身的毒害,需要用许多药物来辅助烧炼,以制伏金石丹砂的易燃性、挥发性、爆炸性和毒性。比如用石膏粉末作为上下铺垫来炼丹,或者把几种草烧成灰,浸成灰碱液,用来拌和丹药。醋、盐和很多植物以及肉类、油脂等都会被用来作炼丹的辅助药物,豆浆也是其中一种。所以有学者推测,当这些辅助药物使用后被当作垃圾倾倒出去,留贮山间坑洼处的豆浆,就有机会和辅助药物中的某种物质混合,比如石膏所含的硫酸钙与卤水中的氯化镁具有同样的作用,于是蛋白质凝胶便自然结成了。它们就混在山间坑洼处的垃圾旁,有的因为时间较久还生有毛菌,因而被人们取名为“豆腐”。估计最初吃它的可能是一些饥饿的穷苦人民。后来人们终于发现了这种“凝胶”的可口,有条件的人便用大豆磨浆来试制,大概是得到了炼丹士们的指点、启发,最终用石膏、盐卤制成了豆腐。
使用凝结剂将豆浆凝结成豆腐,这道工序自古便被称为“点浆”。其实“点”字最早本是炼丹家的术语,比如炼丹家用砒霜来“点”铜为银。“它被用来指称制豆腐的重要工序,说明这道工序的命名最初是由炼丹家提供的。”有学者说,“我国有些较大的中药店号制造外科药物至今还有古代炼丹家使用的升、降法的痕迹,他们在炼制砒霜时,还要用豆腐收伏有毒的气体。这种方法,也是炼丹家传授的。”那么,当年豆腐制成之后,刘安是不是也曾试用豆腐辅助烧炼成仙的丹药?
不论是普通农民在长期的煮豆磨浆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豆腐的做法,还是中国最早接触“化学反应”的道家方士们指点启发了豆腐的制造,不少专家都认为,做豆腐磨浆、煮浆、点浆等重要步骤所需的条件,在汉代已经具备。
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密县打虎亭发掘了两座公元2世纪左右东汉晚期的墓葬遗址,墓中画像石上比较清晰地呈现出当时人们制作豆腐的场面。
自1982年起,农业考古专家陈文华先生数次前往河南密县,对打虎亭汉墓描画这些工序的画像石图案进行手绘、拍照。1990年,“第五届中国科技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英国剑桥召开,陈文华先生在大会发言,向众位国际科技史学者解读了这幅画像以及依之绘制的示意图。自此,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画像,算是在国内外确立了一种声音:至少在东汉,中国人制作豆腐的技艺已经相当成熟。
反对的声音也有,比如化学家袁翰青先生、文物专家孙机先生。争议的焦点大概在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矛盾。至今发现最早的有关豆腐的记述出自五代末年至宋初时期,当时一位名叫陶谷的士大夫写了本《清异录》,说自己在青阳(今属安徽芜湖道)做县丞时,“洁己勤民,日食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袁先生认为豆腐制作最早不过五代。反对的声音还提出质问:“一种五代之前数百年间汗牛充栋的文献典籍中从未有所反映的副食品,忽然被说成已在东汉末年出现,难道不应该认真加以审视?”孙先生就认为打虎亭汉墓画像石上画的不是制作豆腐,而是酿酒工艺流程。
有关豆腐出世的时间、地点,也许将来还会因为某个文献的被发现或者新的考古发掘而再现新亮点,豆腐的身世之迷将逐渐被解开。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其实,豆腐无论是汉代就有了,还是到五代才出生,对于我们这些仰赖先民的智慧可以自由享用豆腐的普通人来说,影响不大。我们可以继续吃各种各样的煎豆腐、炒豆腐、东坡豆腐、麻婆豆腐,而不用靠嚼食煮熟的大豆粒充饥。现代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吃大豆粒食,蛋白质吸收率只能达到65%,而制成豆腐,蛋白质虽然损失了一小部分,但吸收率可以提高到92%-96%;而且大豆含有胰蛋白酶抑制素、皂角素等物质,人食用后容易出现胀气、消化不良等症状,制成豆腐后这些有害物质就被破坏掉了;以素食为主的中国人把营养丰富、口感好、又容易被消化吸收的豆腐,纳入到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中,形、色、味变换着,大大提升了大豆食品的口味,“豆腐百珍”又相映成宴,中国豆腐文化已是世界饮食文化的特殊标志之一——“豆腐的问世,是很了不起的事!”被我问及的专家学者在这一点上没有争议,口径一致。
美国人尤金·N·安德森所著的《中国食物》中这样写道:中国人长期生活在饥荒和营养不良之中,积累了与之相关的无数观察材料,从中创立了民间营养学,也是精英的营养学。中国的确是个自然灾害发生特别频繁的国家,世所罕有。据《中国救荒史》一书的统计,自汉初至1936年,平均每4个月左右就发生一次自然灾害,且大多发生在先民聚居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再加之人为的战乱纷扰,中华民族的祖先所走过的生存之路何其艰辛,可以想象。这样的环境也造就了中华民族耐受苦难、富有韧性的性格。为了生存,先民们创立了就地取材、顺应自然的“营养学”,它自成体系、奥妙无穷,“以食养生”就是一大特色。李里特教授对于美国人的这种说法还有另一种解说,他认为,在西方传统的以肉食为主的人们眼中,一向素食的中国人就是“营养不良”的;西方人以往并不懂得,我们中国人“青菜豆腐保平安”的贫寒的生存哲理,却是至上的养生宝典:青菜提供多种维生素,豆腐则给予了充足的优质蛋白质。这种扎根于民间的营养学,的确堪称“精英营养学”。“如今,西方国家也在自己的膳食指南中提高了蔬菜、豆腐的比重,但是,以他们的饮食习惯,这样的转变比较难。”李里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