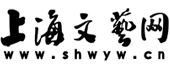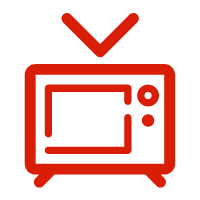抛开一切奇迹的可能,我们一直在出逃——我们的精神空间、生活肌理;我们的思想;我们持续不变的永恒变动;我们无限浅薄又无限厚重的远与近、失与得;我们的价值立场与生命意义;还有我们完全不同又极其相似的生存境遇;我们自由而美丽的诗和远方;我们的精神聚焦与共振;我们深入浅出的生命交叉点;我们日复一日的岁月之光;我们无一例外的新的生命与冲突。
一直以来,在诗歌中,用来测量灵魂和现实关怀的绝不是古代埃及的羽毛,而是诗人们客观存在又不可替代的个体气质与艺术天性。高原与落日,无不在时间与空间的抽象概念中充分迥异了演绎与归纳的差别。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叙事者。在形象、意象分明的排列中,建构的形体与对等物规模宏大而不确定。命运的终极存在与感知,使它们相互作用,又表达自我。他们是思想上的异族。羁旅愁思结合社会意识在诗人的岁月闲暇中,悄然打开了他们的初始部分与旨意,使他们拼命回望又漫无休止的追求,某种积极因素在精神的天堂淬炼而令人着迷。
安德烈·维莱尔在《我们的形象史》中曾阐明过这样的观点,他说,墨丘利和武尔坎代表着两种密不可分,而且互补的生活功能。墨丘利代表共鸣,武尔坎代表聚焦。它们既对照又互补,很像存档在我们所有人心中的故乡和远方。
人生在世,行走而已。于是我们上路,踏上一条所谓的“逃生”之路,带着对未来的期许与精神需要背井离乡成为我们自己的转向者。一边急于蜕变到物我两忘,一边又在前所未有的狂热中患得患失。仿佛苏格拉底,既祈求去往彼岸世界的路上一切顺遂、愿望得以实现,又极其惧怕从此切断自己的精神后援而无颜相对。于是拼命努力、奔突、回溯,然却从不肯离久情疏。他们在语言的象征与隐喻中掀开了写给岁月的诗笺,也奏起自己略带忧伤而固有存在的咏叹调。
《王世明短诗选》正是带着这种生命记忆与温度寸寸游走,“与他人共在”也好,“独自存在”也罢,“新衣旧袍”于他的诗文中突然立体起来、对照、互补。源头活水,搭上人生轮渡,既激情了笔墨,也给予他故乡和远方以确切的描述。
王世明,一九七O年生,辽宁盖州人,军人出身,资深媒体人,诗书画研习者,现居北京。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美国西肯塔基大学孔子学院“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贡献奖”获得者。诗作曾获辽宁《辽河》青年文学奖,入编《2002中国诗歌选》《2008中国最佳网络诗歌》《中国民间好诗2016》等选本。出版有报告文学集《刻进大山的爱》、诗集《王世明短诗选》(中英对照)等。
《王世明短诗选》共收入诗歌三十首,每首诗既孑立又并立,且相互联系。主体共体彼此认同,家国同构,亲情、爱情、追忆,所涉及的生命部分不可控制也不可忽略。在或深沉或明快的聚焦下,他的诗篇共鸣着世人的情怀与感受,但又不断重复确认着指向。故乡、远方,像是不可逆转的洪流,将他的生命行为自然演变,得出互相矛盾的结果。尽管他的诗风于不同时代下有着不同的艺术呈现,但依旧不影响他缔造简约鲜明的视觉形象。这本薄薄的册子,收入的诗作不是很多,且年份的跨度也比较大。从他标记的日期看,他应该很早就做了北漂。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故乡和远方就已经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相互整合了。
如果说,故乡是人生的第一命题,那么远方就应是人生的第二命题。它们互相缠绕,不可分割,决定着每个游子行走的姿势与过程,也让它们看起来更像一对同船而行、抱团取暖的兄弟,既互补又相互对照。这一点在王世明的《望儿山》一诗中有着最贴切的体现。他说,“在你身旁时/我离你很远很远/当我身处南洋/你却就在我的眼前。”
短短四句,却道出了他真实内在的声音。“望儿山”是诗人故乡一个典型的文化名片。之所以用望儿山命名,其旨意自不言而喻。他是在借用“望儿山”来影射他的故乡。没有明线直陈,但也一目了然。
无论身处何方,我们都在向往的路上——从一座山望向另一座山。美好愿景仿佛卡尔维诺提出的空心戒指,永远只会在某种缺乏或缺失中才会得到更多的体现。
他在《华裔》一诗中说,“为梦想/浪迹天涯/却用一生的时间/寻找妈妈。”这里的“妈妈”是祖国,同时也是故乡。
在这首感怀诗中,他用一种近乎白描的本色呈现实施了对比衬托,在“天涯”与“妈妈”之间既复合交融,又袒露出寄情于灵魂深处的那份沉重。短促而意赅的诗行对应着冲突的情感,令他的诗在一种妥善处理中完成了徐徐落下的平静。没有空谈浮夸,没有过度挖掘与起伏。存在的根本与具体现实将主题的属性完好地表达出来,同时也不觉对照与互补了故乡和远方间的关系。
然而,作为岁月激情的笔墨,故乡并不一定是一切的中心,但一定是游子心中潜在的、挥之不去的回响与咏叹。是抒情的忧伤,是阿拉贡口中“既笑得浑身颤抖,又止不住眼泪上涌的剧情。”我们曾钟爱过,也排斥过。那片浓郁的土地,被我们几近抛弃,又几近拾捡。我们所趋的立场、真实的自我,时而在故乡的天空眺望远方,时而在远方的大地回望故乡。仿佛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拼命想出去看世界,而外面的人又在经历一切后拼命向往故乡的怀抱与安稳。思想一直在“矛盾的发展”中逃离或对抗,一种自我博弈的疼悄然生成。
王世明的诗,清新流畅,属于显明的短句式表达。在普遍的观照中,他生命的个体更像是一种声音的传递者。客观而真实的艺术呈现,简洁明快、毫不拖沓,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体验中自由游走。在他的笔下,那些路径与初衷已然成为他的精神养料。故乡是他摸着诗行可以回家的生命流,远方则是他作为鸟的后裔而飞翔的理由。故乡、远方兼而有之,在他的光阴故事中不断遇见又不断分离,相互碰撞又相互摩擦。一种“他乡容不下肉身,故乡安置不了灵魂”之感迅速植入了他的心境。假如当年他没有出逃,那么现在用一生时间追寻的会不会是以梦做象征的咏叹呢?
这或许是一瞬间的直觉,但它却在《飞翔的男人》一诗中形成了这种可能。
他说,“我是那么的渴望飞翔/就像花儿有蕾/要尽情地绽放/就像草儿有绿/要把盎然的生命张扬/我是那么的渴望飞翔/哪怕风雨/一次次打湿了我的思想/哪怕寒流/一次次冰冻了我的心房/哪怕恶浪/一次次折断了我的翅膀/我依旧选择飞翔/因为我是鸟的后裔/我的家,在高高的蓝天上。”
从这首诗不难看出,他当初欲离开故乡时的决心与迫切。故乡似乎真的桎梏了他的飞翔,无论前方有怎样的艰辛与阻隔,他都要寻找自己的蓝天,寻找他视以为家的远方。而这种渴望,在《我是一个小小的京漂》一诗中也有同质的呈现。
他说,“……我是一个小小的京漂/我知道我的旅途/没有通天的大道/明知道青春是退色的云裳/我还是要带着梦想飞翔……”
在这之前,他好像已于故乡和远方间做了权衡利弊。做京漂只是他对照后的态度与决定。而诗的结尾,又与《老屋》一诗的结尾建立了联系,呈现出他模凌两可的境遇。他说,“……当有一天我老了/当有一天我不能飞翔/我希望倒下的地方/冲着家乡的方向。”“而今,身处异乡的我/已不再迷惘/却不知该在哪里/为老屋立块石碑。”
一种可见的、无法安顿的怅惘跃然纸上。他的家注定在远方,而故乡,只是他曾经的一个过去。故乡、远方同时在路上,既相悖又彼此烘烤。它们是岁月的烈酒,是人生的驿站,是沉默的文字,是不可遏制的对照与互补。
他是故乡“失落的鸟”,无论身处何地,他都是村口小河里那个光着屁股捉鱼的小男孩,那个憧憬天堂的过客。
而故事的真正主角既是写作者又是被写者。在叙述中,他用“武尔坎的专注和技巧记录了墨丘利的经历与情志”。不但令故乡和远方彼此呼应,也令他的诗行和心里产生强烈的感情反差。他的诗或直陈意旨,或暗示文眼;或表情达意,或晓明通畅。在实际感受与尚未表达的存在中,他转动的命运之轮抖落了身上的焦虑,并结合词语的建构最大限度地营造了一种时空的艺术感,既得以诗意还乡,又于生命的地域中完成一次次的精神对接。他的诗轻巧质朴、结构精致,是那种看一眼就会喜欢的诗句。无论时间、地点切近或遥远,他思想感情的交流都会像伽利略一样,在纸页上千变万化地排列……
媛婕嫣,原名张金芝,辽宁营口人。系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中华现代文学艺术促进会理事、北京写作学会文化艺术促进会理事。2017年进修于辽宁文学院。作品散发于《中国铁路文艺期刊》《阳光》《中国诗人》《天津诗人》《辽宁诗界》等报刊,曾获白天鹅诗歌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