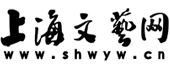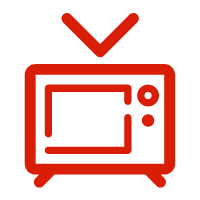小说家是有性别的——哪怕是考虑到美国人跨性别、双性别、伪性别等多达数十种的性别分类——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毋庸置疑的。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存在部分的偏移和偏差。那么,小说有性别吗?刨除纷繁芜杂的性别型,简而言之,存在“男小说”和“女小说”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答案是肯定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你好,忧愁》、拉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与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阿兰·罗伯·格里耶的《约会的房子》、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一定带给你迥然不同的性别感受——小说是有性别的,阅读也是有性别的。同样是写上海,夏衍和张爱玲是不同的成色,金宇澄与王安忆文本的性别特征昭然若揭。
女权主义发展到世纪之交其实已经自觉地“钝化”表述为女性主义,更强调性别自觉和性别立场,弱化与另一性别分庭抗礼的火药味。也确实,不论是当今社会还是远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社会,两性别杂糅共生是天然的现实,敦睦好过对立,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可能是两性别勾连的那条唯一恰适的路径。性别革命、性别觉醒基于男权社会几千年累积在血液里的集体无意识偶或有意无意的冒头,出于自保,这种性别革命和性别觉醒反应过激、矫枉过正在所难免。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对于女性性别的过分强调反过来恰恰又将自己的性别置身于弱势、式微的一方——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悖论,女性性别自觉造成自我性别矮化的后果,从而达成与“男权”殊途同归的同谋。这也就是不少事业女性如总裁、画家、装置艺术家、作家、诗人、导演、演员不喜欢在自己的职业、职位前面冠以一个“女”字的原因,也是我为何不大主张打性别牌,抵触“女性写作”、“女性表达”、“女性叙事”这类带着强烈性别标识的标签。
当我们强调女性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时,可能忽略了另一性别其实同样具备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当我们捍卫“女性思维”模式和敏感、细腻、感性、较弱的逻辑性和思辨力、相对敏锐的洞察力这些“天生具备”、“生而有之”的“女性创作特质”时,不知道其实已经滑入了女性主义为之抗争的男权意识。何况,谁说以上特质乃女性/男性作家专属,男性/女性作家就天生缺失?有几个女人能够敏感、细腻、感性到像普鲁斯特一样几乎足不出户就能写出窗帘外的世界?米切尔、杜拉斯、萨冈、麦卡勒斯、张爱玲的逻辑和思辨只是被大时代的迷情、天赋的才气、浓郁的个性笔调所遮蔽,她们笔下从来不缺逻辑不缺思辨。而说到女性作家的主体性,从“我”出发去体认“我”、体认人、体认世界,几几堪称天道——难道还有无“我”的创作?哪怕是被地理学、想象文学等等学科门类追认为鼻祖的《山海经》,或是《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志怪志异小说,《封神演义》《西游记》及至当下执“超级IP”、“头部内容”牛耳的《盗墓笔记》《鬼吹灯》《藏地密码》《龙图腾》《西游传》等等玄幻、奇幻玄之又玄的幻想文学,无不植根于现实、历史的坚实土壤。正是由于性别意识的自觉,又清醒矫枉容易过正,我保持着对于他性别弱化、钝化、矮化的警觉,我笔下的女性角色固然写得活色生香,饱满充沛,生活气息浓郁,或高扬理想主义的大旗,我取材、提炼自生活再加以艺术改装、创造的每一个男性角色,也杜绝脸谱化、偏平化,拒绝“纸片人”的本质一方面是艺术追求,另一方面是拒绝性别歧视。我在成为小说家之前是诗人。从诗人到小说家的转换,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华丽转身、应对裕如。我之所以转身从容,可能得益于我有几副笔法:将诗的归诗,将小说的归小说。我的经纪人丹飞就称道我多面手的这个优点,因为省去了矫正、校正的麻烦。我的中短篇小说结集为《三个女人的咖啡》,我迄今创作了两部长篇,一部《无法刹车》出版了,主题是大热门主旋律:养老。丹飞给改名为《向着那光明》,我持保留意见;一部还没出版,写老上海的人间烟火、光影声色,我起过《老城厢》《红泪》等名,丹飞改名《弄堂深处有人家》,我觉得改得吸引人。本质上,我认可他的一切策划、包装、操盘,用他的话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专业是“码字”的,“码字”是他的爱好,是他的娱乐活动,他是专业成全我们码字的。总之,写作上,我所有身家都交代给他了。他是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后宫——甄嬛传》《戒嗔的白粥馆》《政协委员》……的总编辑,影视剧《甄嬛传》《王阳明传》《匈奴王密咒》《牺牲者》《白泽图》《兰陵缭乱》……的IP经纪人,《狼图腾》全版权孵化的合伙人兼副总,他也写过电影电视剧,我相信他耀眼的成绩单上可以增添关于我的一两笔——改名后,两部长篇明显有了IP相。细想想,我的小说创作中何曾强化过自己的性别身份呢?犬牙交错又相安无事,大概是两性交驳的理想状态。
我的这种体认有着大量同盟军。刘慧英在《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一书中说:“我反对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我也不赞成男女两性长期处于分庭抗礼的状态之中,我比较赞赏西方某些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建立和发展‘双性文化特征’的设想,它是拯救和完善人类文化的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道路。”铁凝在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文联主席之前是勤奋的小说家,她表达过类似观点:“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当你落笔女性,只有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的自赏心态,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身为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创始人之一的伊莱恩·肖瓦尔特对于超越性别局限进行反拨:“想象力逃脱不了性别特征的潜意识结构和束缚……不能把想象力同置身于社会、性别和历史的自我割裂开来。”——如何基于性别事实,又不囿于性别藩篱,是写作者需要长期摔打历练的课题。这个过程中会有隐秘之欢,也会有龃龉之痛。如果说我和我的小说有性别的话,其性别不是女,是“我”。(作者:陈佩君)
责任编辑:杨博 沈彤
新闻热线:021-6131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