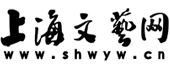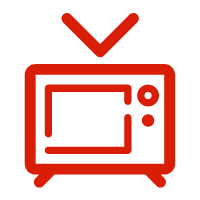凡来宾都会在走廊及书房里悬挂的水粉画前驻足,那里有山水静物、人物动态以及领袖清晨登庐山风姿……都以为我曾就读于美院,其实不然,说来话长。
握笔蘸色涂画起于“文革”年间。
起初迷茫。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于华师大毕业踏上市重点中学讲台,正准备尽绵薄之力,不意风云突变,文革风暴掀起,停课闹革命,我自然积极响应,但是困惑:革谁的命?土改革地主的命,“四清”清经济账,“文化”怎么革?据说革走资派,那谁是走资派?据说在上面,那我们老百姓也够不着啊!再说以往的运动都由领导指导的,现在连领导也莫知所云,大家都像没头苍蝇。团市委派来工作组,急忙去请教,没想到那位副组长竟然也说不清楚,上面只说进驻就来了。全校令人窒息地一片沉寂。
接着不解。暴风雨之前的宁静毕竟短暂。某晚正在捉摸大革命的精神,高三教学楼忽然爆发震天响的“万岁”声浪,赶紧去探听,原来广播里传来今年高考暂停消息,那年头大学是培养精英,入学率不高,学生压力山大,这下“紧箍咒”解除了,自然兴高采烈了。我们在疑惑:高等教育不办了?然而此令奇效立竿见影,高三学生全无后顾之忧投入运动。第一号行动就是抡起大锤把校园内的所有石狮子执行砍头刑,迅即又发出第二号令:勒令全校教师上交金银首饰。高三大哥大姐带头冲锋,低年级弟妹便有样学样,勒令教师敞开大门,让小将入门扫四旧。我化了首份四十五元工资的五分之一买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精装本竟被清除,说苏联是修正主义,那么那里的人也都不是好货。《红楼梦》也差点遭殃,说为什么不取名“红太阳”,但因有个“红”字就“取保候审”——暂留我处。
原盼望工作组能掌掌舵,没想到悄悄地撤走了,这下局面就完全失控了——实际是向纵深发展:转为对人不是对物:校长被说成是走资派,监督劳动。他只是小小的基层领导而已,敢走吗?能走吗?这是一,其二:所有教研组长一律升级为反动学术权威。这些普通的教师突受如此恩宠都莫名惊诧,也全都享受监督劳动,送入牛棚。本人为青年教师,三门出身,享受此誉不够格,属于争取对象。众人大惑不解:这算哪门子革命?继而不满。此时由红卫兵团掌控局面,运动很快由只动嘴成转为动手了。某天中午正在午睡,窗外忽然飘入两名初中生耸人听闻的对话:“我X他妈,我老爸也被揪出来了,没想到斗得最凶是那条犯了错误挨老爸狠批的狗,他乘机泄私愤极复!”“咱妈也是,斗我妈的是没本事却想当头的下三烂,说我妈压制工农子弟!狗屁!”“我真想拿刀捅了他。”“不行的,现在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沉默,我知道他们是市委干部子弟。“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要不揪个教师斗斗,出口气!”“这一招可以,大方向正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嘛!不过得先成立一个战斗队,表明是组织行为,不是报私仇”“对!就叫‘打狗战斗队’。”“还有最好跟红卫兵团头头通个气,就算是他们的一个分队,我们底气就足了。”
他们第一个“革命行动”的对象是位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外语女教师,因其气质高雅、容颜姣好、被人羡慕但也不可避免地遭一些人妒嫉。给扣顶资产阶级少奶奶的帽子,绞了花格衬衫、窄腿裤管,剃了个阴阳头,还让她低头认罪:“触灵魂,好得很。”
岂止受教育者如此,施教者中也不乏其人,成立了教工造反队,与红卫兵团协同开展运动,但毕竟非不更事少年,懂得策略,不抛头露面,而到学生中放空气、抛材料等等,把运动推向深入。
面对这种局面大多数不解,认为学校以前状况很正常嘛,不应推倒,这种舆论当然不被容许,被批为“保皇派”,于是争议蜂起,谁也说服不了谁,造反派故技重演,到学生中去点火,于是出现这样一幕:一位旗帜最鲜明的披小将押着在校内游街示众。那是一位个头不超过一米六十的瘦弱女子,头上却戴了顶几乎与身等高的纸帽子,又给了一根一米多长的粗铁棍,责令她边敲铜锣边高喊:“我是保皇派。”企图让她出洋相,杀杀她的威风。谁料她却面无愧色,竟然巧妙地拿轻便的铜锣倒过来去碰笨重铁棍,赢得围观师生暗暗称赞其头脑灵活,一场闹剧却只落得幕后策划者失落,然而群众中的鸿沟更阔更深了。旋即革委会成立,人们发现某些人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权力舞台,却特意让食堂烧饭的当一把手——相当于校长,以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这更引起纷纷议论:他怎么能带领开展教学?但这是必须的安排,不然通不过;谁清楚某些人葫芦里卖什么药?但一无结论,只能默然接受,但也就从不满转为悄然退出,出现了一批逍遥派,在持续批斗会之余,女教师关起门来大谈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文峰塔下》、《绿色尸体》……男同胞则打纸牌:杜洛克、80分、桥牌或侃大山……敞人也就此时学会打桥牌的。
不忍退出。革委会成立后首次取得清理阶级队伍的重大成果,在外调中挖出在数学组的国民党党部委员。为扩大震慑效果,采取事先秘而不宣,而在全体教职员工大会突然抓捕,造反派冲上去像抓贼似的反剪那人双臂、抓揪衣领押上台,压成火箭式套上高帽,他猝不及防,吓得脸色煞白,满脸冷汗,全身抖得像筛糠,勉强侧过头着颤抖着声音申辩:“我不是……”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当即打断他话头高呼:“敌人不老实怎么办?”底下齐声高呼:“打倒他!”“再踩上一只脚!”一名年轻的与他同组的造反派抬起穿皮鞋的粗壮的腿刚要往他头上踩,见到我频频摇头才没往下踩。头头下令把他押下去,监督他先打扫女厕所,接下去作报告:“革委会刚成立就初战告捷,会开得很成功,大张了革命派气势,但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还要继续,更要深入……”我没听完,中途悄悄的退了出去——事后发现抓错了:同名同姓。
不甘沉沦。自此凡遇到这样场合我总找各种理由避不参加:实在于心不忍,但过不多久就落入沉思:难道就这样下去?我才刚到而立之年,拿什么去立?早已停课闹革命,教师全部被“失业”。那时唯一还需要动动笔头的就是写大批判文章,写赞颂“文革”的必要与及时,批四旧立四新文章,并且选取精华编成专栏,展览到校门口及县里热闹区的大街上,这倒颇有点文化味道!这让我回忆起中学年代,那时我是学生会宣传部长,每逢朝鲜战场捷报传来,我立即放弃听课,制作跨街祝捷报横幅——那时是先在白纸上划字样再裁剪成后黏贴在红布上,颇费功夫的——再出专栏黑板报。由于捷报颇传,以致缺课太多落入补考,但我乐此不疲。我想重操旧业,这正中下怀,不想一拍即合,革委会头头正在物色人员,因我既能文也能画,这样就可以只一人不参加批斗活动,我终于如愿以偿了,不料一下水就不想上岸了。
造反派头头拨给我可坐五十多人的大教室为政宣组办公室,因为耍铺开整张白报纸誊写文章。环境开阔舒适,又远离开批斗会的礼堂,征文、审稿、编排、美工、组织人员誊写与张贴等均为一人独掌,被我请来誊写的都有一手好毛笔,且大多是逍遥派,我与他们平起平坐,只是互相配合协调关系,偌大的空间便宁静和谐,窗外绿荫覆盖,时而鸟鸣林间,偶面飘来的口号声也是隐隐的,这儿似乎成了世外桃源,十二级台风的风暴眼。
岂止如此。我在编排大批判文章外,辟设副刊,编写花絮之类短文,给凝重的版面增添些色彩。例如那时京剧当红,我就编写五八年上海京剧院赴巴黎演出的盛况。法国人报道有个特殊标准,因法国人较浪漫,看得满意时便扭动身子以致损坏座椅,报道就以扭坏座椅多少来评判,上海京剧院演出导致损坏的数量远远超出由芭蕾女皇乌兰诺娃领衔演出的芭蕾舞剧经典的《天鹅湖》,而法国是芭蕾的发源地。又如那时谈及阿尔巴尼亚常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古诗,但这“天涯”究竟有多远,那时松江只是个农业为主的县,较闭塞而文化程度偏低,我就画了幅简明的世界地图,用双头红色箭相连……令我兴奋的是,这些一上街,专栏前就人头攒动,文章内容就成了人们的谈资。我深受鼓舞,一发不可收。
与人乐乐。某天,我随同擅长裱糊的许师傅布置好新一期专栏回校,正好撞见那位女教师、头发斑白的瘦个历史教研组长等在烈日下劳动,衣衫全湿透了,我禁不住一阵心酸:大家共事多年,我自悠哉,人家却遭罪,如果无动于衷,不伸援手而独乐乐,我还是个人吗?我借口他俩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向头头请示是否让他们也参与誊写,强调字漂亮宣传效果就更好——我这是抓住他们刚掌权急于要显示能耐的心态而说的,我再添加一句:誊写大批判文章也是触灵魂。谢天谢地,此请求被恩准了。
一计得手,再施一计。我对誊写者严格规定:字必须写得端正,否则重来,凡抄错一个字或越出规定范围一律重抄,他们笑骂我是“包工头”,可心里却美滋滋的,他们心里明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延长这难得的有尊严的时间,呼吸自由空气,多享受和谐氛围。接着我又得寸进尺,缩短发刊周期,这样人手就不够,就抓“壮丁”扩军——从监督劳动者中要人,以致偌大的空间坐得满满当当。他们开始虽然心情舒畅却较拘谨,后来发现我不是头头,而是“中间派”而已,也从不去汇报,相反是拉自己于尊严天地,便谈话声渐起,有时还谈笑风生,有的还早早地前来,笔端笔正地誊写,然后又跚跚离去。
此刻我便在一旁给誊写好的添上彩色标题,空隙处配上图案花卉,然后画大幅刊头画。放下画笔,回首抚视埋头却舒心执笔的同仁,我满心宽慰,于是拿起画笔“借公济私”——临摹自己喜欢的画。由于非科班出身,爱好而已,心中无底,故先从难以较真的静物花卉开始,形象色彩差一点无所谓。我在牡丹花冠上的蜜蜂、绿叶上的露珠颇下功夫,受到称赞,信心就起来了。想起杜甫“行万里路”的诗句想象联翩翩,那年头旅游只是美丽的奢望,那何不在画上畅游呢?“画景充游”也是人生一乐!我画了桂林山水,又按照春夏秋冬画了颐和园的宝带桥,北戴河海滩、杭州西湖夕照、断桥残雪。每每誊写告一段落,人们便观看我临蓦照片作一番神游大地,调节一下压抑的心情。
某天,新的一期专栏完工了,人们都悄然离开了,但毕业于浙大的年长的历史教研组长留了下来,真诚地提醒我:“别老画风花雪月”。我一愣,注视老前辈,看到的是满眼关怀。“现在又是文革期间。”他又加了一句。我清楚他是以这种言辞来表达对我把他从监督劳动中“请”出来那怕是短暂的自由的感谢,但我感到说辞有些意外,他不正是运动一开始就被勒令靠边站的吗?不料他这样回答我:
“人生百年,怎能不磕磕绊绊的。”
“可是您老多年来一直勤勤恳恳呀,从不侵犯人,却遭此冲击,而且斗你最凶的是水平不高的,您不委屈?”
“按照历史学观点:当代人写不好历史,因为排除不了个人恩怨,况且我又是一介平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局面不能失控的,一旦失控就难免泥沙俱下,沉渣泛起,任何时代失意的不得意的永远会有,你看眼下这批积极分子有几位平时都因种种原因不被关注,现在机会来了当然想冒一冒,历史上为什么总是农民起义?就因为相对地主达官贵人,他们是不如意的一群,像我当了组长有组长津贴,还享受到景点休养,他为什么没有,不是一样上课吗?自然不平,不平则鸣,可以理解。”
老前辈说得很平静,似乎是在上历史课而不是在谈亲身切肤经历。我依然不平说有人就利用人性这一弱点挑动人为他服务,那个头头不乘乱登上舞台了吗?
“没什么,时间会发话的,何必争一日之长短。”
他瘦骨嶙峋,双目却明亮和蔼,透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胸襟与见识,禁不住肃然起敬:“您老真大度。”
临走之时再次叮嘱画点红色的,我懂他对晚辈的拳拳之心。我手头正好有一幅领袖清晨登上庐山顶的油画:蓝天白云,青松相伴,敞开大衣迎着朝阳迈步登顶,堪称上品,决定以水粉临摹之。当我精心画领袖手中一缕缥缈的青烟时,窗外隐隐传来大会批判声……
圆满结局。风暴过后艳阳天,县里召开中小学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大会,参加者佩戴大红花在大街上进行,接受群众夹道庆贺,在大会上要求即席献诗,我登台高颂《红花之歌》,获得全场喝彩。
更让我们没想到,几位正宗的科班出身的美术教师热情鼓动我参加画展,我真是受宠若惊,但也想一试,显示文革的意外成果,特意创作了两幅,连同临摹的一起送展。等到画展结束,清点画幅时发现原创的都被人拿走了,人间还是有欣赏水平高的,这就是如今我家走廊上得以悬挂《桂林山水》的缘由,“劫”后余生啊!
2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