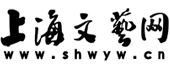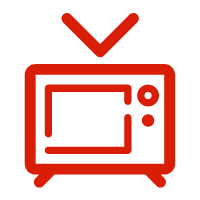“他是哪个部队的?”我问护士。“据说是警卫队的领导。”护士端着托盘,边回答边准备进手术室。“警卫队”这三个字在我脑海中一掠,就像一道电光一闪。莫非是江琦?“他叫什么名字?”我急速地问。“姜齐”,护士说完急急进了手术室。
什么?江琦,我疯一般地冲进手术室。正在手术床前弯腰做手术的院长猛地抬起头,显然是被我突然闯进吓了一跳,带着疑惑看着我。我顾不得向院长解释,就向躺在手术床上的伤员探望。那伤员紧闭双眼,黑黢黢,脸色铁青,面无表情,头发乱糟糟,下半脸满是胡须,看样子有30好几。这不是江琦,我再仔细查看,肯定这不是江琦。一种失望涌进心头,心凉了大半截。院长已经明白了我的举动,说这是纵队警卫大队的大队长姜齐同志,老姜的姜,整齐的齐。院长的眼里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我低下头,缄默沮丧地走出手术室。老天实在不该如此捉弄我,痛楚的伤口又被刺了一下。
夜晚,我又失眠了,瞪着屋顶发呆。江琦啊,你为何如此飘忽渺茫让我揪心,莫非你真的已经离开人世,去了另一个世界?不可能,在没有见到尸体之前,江琦就不能与死亡划等号。可江琦究竟在哪儿呢?被急流冲走?在深山养伤?成了植物人?我这样想着想着,直到天色有些发白,才迷迷糊糊睡去。第二天上班精神不振,院长看到我这样,没说什么,摇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我知道院长在为我担心,不觉心中一阵无奈和内疚。
傍晚,陈老师知道了此事,不放心我,赶来看望。我们坐在四明湖边默默无语,我知道陈老师失去梅纹后,你心中的痛苦绝不亚于我,现在我们是同病相怜。之后的一段时间,陈老师一有空就来看望我,我渐渐平静了下来,似乎对他有了依赖,总将一些心事向他倾述。有时,他也握着我的手倾听我的叙述,他的眼神善良温馨,好像有江琦的影子,他的手很热乎,热量传到我的身体使我感到了温暖。一天傍晚,我们坐在湖边草地上,晚霞映在湖上,在湖水涟漪中划出道道亮线。一对鸳鸯在水中嬉戏、漫游。陈老师若有所指地说,鸳鸯成双成对不可分离啊。我突然想到江琦,说,我和江琦就是一对鸳鸯。说完,我后悔话说得太直白,偷偷瞄了他一眼,正巧与他眼光相撞。看到他若有所思,我赶紧补上一句,你和梅纹才是真正的一对鸳鸯。我又提到了梅纹,触到了他的痛楚。真是越慌越乱,我不好意思低下头。心里却在想,江琦是我这一生的最爱,我只能把陈老师当成大哥哥看待,江琦一天找不到,我就一天不死心。一阵风夹杂些许寒冷吹过,我不禁打了一个冷颤,陈老师拉过我的手说:“天冷了,你手也凉了,我们回去吧。”说完起身拉起我。
几天后,陈老师带领三大队几十名战士,在青山集与前来抢劫的鬼子打了一仗,消灭了全部20多个鬼子,这一仗打出了威风,鬼子怆惶丧胆,老百姓大快人心。鬼子对新四军恨得咬牙切齿,山佐大队长气得哇哇直叫。
凌晨,院长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昨天夜里,陈政委在县城袭击鬼子时负了重伤,现被隐藏在县城,急需医院派医生去急救。我换了便衣,顾不得吃早饭,梁大娘给了我一个山芋,我边吃边上路了。来到县城门前,我们排在被检查的队中。几个出城的人在我面前走过,他们看上去都是当地的农户。我进过县城几次,对付鬼子和伪军的盘问已有了经验。这时,一个出城的农民突然紧盯着我走过来,我心里正疑虑,就见他神情惊异走到我面前,仔细打量我,似乎发现了什么。门口站着许多日伪军,周围似乎还有一些日伪便衣在游动,一旦哪个人被查出携带违禁品,或被无端怀疑,便会招致杀身之祸。我心想,这个人莫非是敌特,顿时警惕起来。我用心细看他,他身背一个空竹篓,手里拿着一块用得泛黄的土布毛巾,个头较高,宽肩厚背,红脸膛,大眼睛,额头有块清晰的伤疤,像是被刺刀狠狠戳出来的。他在我面前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觉察到了什么,愣了一下,随即便与我擦身而过。我回头望,见他还不时地回头观望我。
到了陈老师藏身处,我眼前看到的几乎是一个血人了。躺在床上的陈老师身中数弹,腹部、大腿、肩膀都有伤口。一股悲痛袭来,我眼睛潮湿了,想到要快点急救处理伤口,便用手抹了把溢出的泪水,赶紧打开药箱,拿出手术器具和消毒药水,动手为陈老师清理伤口取子弹。我抬起手刚要消毒时,陈老师用微弱的手挡了我一下,断断续续地说,我不行了,不要救了,把药留给其他伤员同志们吧。
我看着陈老师的眼睛,他眼中没有丝毫悔痛,只有坚毅、恳求、期盼。我怎么能不救呢,他是江琦尊敬的老师、领路人,江琦牺牲后,我是在他的开导和鼓励下走出悲伤的。除了江琦,他就是我最敬重、最亲近的人。我的眼泪不顾一切地奔泻出来,我握起陈老师的手哭着央求:“陈老师,您不能离开我,我不让你走。”我泣不成声,可是晚了,陈老师最后看了我一眼说:“照顾好自己”。他握着我的手使劲地攥了一下,随即便松开了,眼中露出一丝关怀、遐想和释然后慢慢闭上了。我急急按住他的脉搏,脉搏没有了,我又快速按住他的颈动脉,几下极其微软的颤动后,也归于平静。我止不住低声抽泣起来,大家摘下帽子,低头致哀,屋内静极了。
赵强说,这次战斗我们准备充分,如果不是汉奸告密,设下埋伏,陈政委是不会牺牲的,他是在掩护部队撤离时中弹的。汉奸,又是汉奸,我问,知道是谁吗?赵强握紧拳头,瞪起双眼,从牙缝中吐出一个名字:朱二。又是朱二,这个汉奸害死了梅纹,害死了陈老师,害死了多少抗日战士,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一股怒火从心中猛地蹿出,我狠狠地说:“我绝不饶恕这个汉奸无赖!”
我们将陈老师与梅纹一同安葬在桃花岭上,环顾开遍满山的映山红,在脱下军帽致哀的那一刻,我从心底发誓:“安息吧。我一定要让汉奸偿还这笔血债!”
我精心挑选了一把锋利的手术刀,那是一把德国制造的,硬度极高的纯钢制品。我把它揣在怀里去找赵强。赵强一听是去为陈老师报仇,就使劲点头同意了。我让他再叫上两个武功好些的战士随我们一起行动。他立即转身跑进营地,不一会儿,两名精干的战士随着他到了我面前。
赵强递给我一把手枪,说,“用它防身。”我坚定地用手挡了回去,“用不着”。赵强一愣,不解地看着我,我说,“我有手术刀!”
半夜,我们摸黑进到镇上,早就打探到今晚朱二会在风荷楼姘头那里鬼混,他常去妓院过夜。这种汉奸连老天都愤恨,那夜老天撒下浓浓黑云迷雾,夜色更显深暗。我们翻墙悄悄进入风荷楼,很快找到朱二与姘头的房间,夜已三更,朱二抱着姘头正呼呼酣睡,口中唾液直流到枕边。一战士用尖刀轻巧地拨开门销,我们冲了进去。那朱二还在睡梦中就被我们捆了个结结实实,堵上嘴巴。那姘头在墙角不停得悉悉索索颤抖,恐惧的眼睛露着哀求。
朱二更是惊恐,扑愣愣张着眼睛,喘着粗气,看到我们手中的枪,下意识地蹬动双腿往角落里躲。赵强一把拖过他,怒视道:“朱二,你的死期到了!”朱二眼珠惊恐得快要跳出来了,嘴巴拼命呜呜,想说求饶话。我拉住赵强说,把堵嘴布先拿掉,看他说些什么。赵强用枪抵住朱二脑门说:“不许叫,敢叫,我一枪毙了你。”这可是无声手枪。朱二使劲点着头,生怕我们没看见。赵强一把扯下堵在朱二嘴里的烂布,朱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饶了我吧,我们都是中国人。”
“呸!你这个败类,你早就不是中国人了。今天,我代表新四军纵队,要你这个狗汉奸的命!”说完,我向赵强使了一个眼色,赵强心领神会,立即用破布堵上朱二的嘴,把朱二按压跪在地上,一只手从后背拎起朱二衣领,一手揪住朱二的头发向后仰去。朱二的脖颈在我面前暴露无遗,我眼前快速闪出梅纹和陈老师牺牲时的情景、江琦投掷最后一颗手榴弹的身躯。国恨家仇浪涛般冲进心头,我盯住朱二,稳稳握住手术刀。刀锋锐利,闪着耀眼白光。朱二被狠狠地按住,他夸张地瞪大眼,眼珠子几乎要掉了出来,身体扭动,两腿哆嗦。倏忽间,一股骚臭味弥漫空间。这小子吓尿了,一阵恶心。我手指捏紧刀柄,举起手对着朱二喉咙。突然间,我的手放了下来,脑中显出朱二被我这一刀割破喉咙后的情景:血从他的脖中流了出来,那不是红色的,是黑色的,肮脏的,带着病毒和细菌,那是我的手术刀割破的吗?我低头看了一眼握在手中的手术刀,小巧、光亮、洁白,那是我用来救治伤员的武器。这把刀救活了不少抗日战士,他们向我致敬,重返战场杀敌。今天,这把手术刀怎么能够捅进汉奸的体内,怎么能让救治了抗日伤员的武器染上恶人的病毒!我收起手术刀,对着赵强使了一个眼色,然后转过身。
当我抬头面对苍天时,听到背后“噗”地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声。我回过头,看到朱二张着嘴,两眼翻白,两腿蜷缩,倒在地上,已经毙命。赵强一枪命中要害。
我站在陈老师梅纹夫妇墓前,郑重地说,安息吧!朱二那恶贯满盈的汉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我们为你们报仇了,为抗日军民报仇了。
姜齐大队长在我们的及时抢救和精心护理下苏醒过来。望着站在床前的我,他的眼神有些茫然,但很快就似乎明白了。他向我微笑,露出暗黄的牙齿。他的脸已经被我们擦洗干净,只剩下从上嘴唇到下巴参差不齐的胡须,这使他显得苍老,可他的眼睛是明亮深邃的,有种成熟的力度。我对他说:“姜大队长,你总算醒过来了。”他笑道:“阎王爷不收我,让我回来再多杀些鬼子。”“阎王爷也知道鬼子吗?”我打趣道。“知道,小鬼子作恶多端,阎王爷早就在地下十八层给他们备好地狱了,哈哈哈!”他声音虽微弱,话语却清晰明了。毕竟是负了重伤的人,刚醒过来,我不能与他多说,嘱咐了几句要好好休息的话,便退了出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乐观自信。
医院伤病员日渐增多,我从梁大娘家搬到医院居住,为的是能够及时全力救治伤病员。
姜齐大队长很快就能下地走路了,他的大腿被一粒子弹穿过,留下一个很深的枪眼,在练习走路时很是吃力。我们用木棒给他做了一个拐杖,他依仗这根拐杖,一瘸一拐竟也能走出不少路。他浑身汗水淋漓,看到我感叹担忧的眼神,笑着说:“这可比我们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轻松多了。”毕竟是经历过残酷战争磨练的人,姜大队长的心理素质确实很好,不久他的身体就能运行自如了,他恢复了猛虎般地常态,随时可以扑向鬼子。夜晚,他常约我坐在屋前树下,用一双粗糙的大手卷起一根用粗黄纸张包裹烟叶的烟卷,吸一口,吐出细丝般旋转飘拂的烟云,然后,津津乐道给我讲红军长征故事,讲他经历的战斗故事,讲他家乡江西红土地的故事。想不到,他还是一个装满故事的人。我被他精彩的讲述所吸引,时常落泪,时常欢笑,又时常沉默,但我不喜欢他抽烟。
夜晚,我又梦见了江琦,他身穿崭新的新四军服向我走来,温馨而博学,威武而善勇。这是错觉吗,我尽力睁大双眼,没错,眼前就是我思念的那个江琦。我向他张开双臂,“江琦,江琦”,我就要抱住他了。蓦地,姜齐出现了,粗矿朴拙中带着乐观骁勇,他微笑地看着我说:“你在叫我吗?”他向我走近,越来越近,呼气中带着烟味,一根根胡须清晰可见。我向他身后、四周寻找江琦,江琦却遽然消失,我心急如焚,连声大叫“江琦,江琦。”猛然惊醒,才知又是一个梦。摸摸头,全是汗。
第二天,我还在被夜里的梦魇困惑。院长见我郁郁寡欢,一脸忧虑,关切地问我是不是累病了,我摇摇头。同屋的护士走过来,对院长三分嬉戏三分诡秘地说:“秦医生怕是有心病了。”
“是么?什么心病,说来听听。”院长显然有了兴趣。“秦医生怕是看上我们姜齐大队长啦。”“别瞎说,才不是呢。”我极力申辩。“还不好意思啦,昨晚你喊了一夜姜大队长的名字。”护士嘻嘻笑着。“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院长若有所思片刻,旋即一拍大腿,连说三声,“好,好,好哇!”
我满脸发烧,急声说道:“你们张冠李戴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可是他们根本不听我申辩,转身走了,小护士还不忘回头做个鬼脸给我。我知道院长不会搞错我说的是“江琦”,而不是“姜齐”,他这样故意,一定是另有含义。不管他如何,反正我说的是“江琦”。
果然,两天后,院长兴冲冲地找我谈话,他一脸正经清清嗓子说:“秦医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姜齐大队长看上你了,他已经向纵队领导提出要娶你为妻。按照我党目前“二十八、五、团”的规定,就是满足年满28岁,参军五年,团级干部这三项就可以结婚。姜齐大队长可以结婚。现在,我代表组织,介绍你和姜大队长的婚事,你看如何呀?”我早有思想准备,我与江琦有约定,打走鬼子,我们就结婚,我要等江琦回来,不见到江琦回来,我不会与别人结婚。我向院长坚定地表示了我们的誓言。院长思考片刻说:“秦医生,你要接受事实,江琦同志很可能已经牺牲了。姜大队长出身贫苦,当过农民做过工,典型的工农干部,很早参加红军,经历长征,作战勇敢,政治上可靠,是优秀的指挥员,这样的干部不多呦。如果与他结婚,你们可是绝好的一对呀!”我相信院长说得真诚,他是为我好。这段时间与姜大队长接触,他的乐观、随意、豁达,还有他所经历的磨难艰险已印入我脑海,但那只是好感,而不是爱情,我的爱在江琦身上,这一点,我始终不会变。我无法接受与姜大队长结婚这个提议,我向院长提出,即使江琦真的不在世了,我现在也不考虑婚事,等打走了鬼子再说。我的话语很坚决,不留丝毫空隙可钻。院长看我如此坚决,也只得叹了一口气,表示惋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们振奋无比,奔走相告,我们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这场抗战的胜利。我来到桃花岭上,带着满脸泪花,望着远处的青山,向江琦呼喊:“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江琦,你说过,打走了鬼子,我们就结婚。你在哪里儿?你快回来吧!”然而,江琦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失望地看着远山迷雾,听着脚下河水激流咆哮,默默祈祷江琦能真的出现在眼前,而不是总在梦里出现。
8月下旬,毛泽东主席赴重庆,与国民党主席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为了和平,共产党让出江南几个省的根据地,撤至山东。接到命令后,9月底,江南新四军所属部队开始了大规模北撤。
清晨,我打起背包,最后看了一眼生活战斗的地方。医院的物品连同伤病员已被运送到船上,医院驻地的庙中已无人员和物品,往日的繁忙喧嚣被宁静替代。我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三年,与伤病员、老百姓和医护人员有千丝万缕的情谊,这里有我思念江琦的梦幻,离开这,我于心不忍。我眼里湿润了,涌出泪水。江琦,我走了,向北走了,如果你回来,一定要去北方找我。我狠狠心,转身向海边走去。海边升起迷雾,那里停泊着运送我们的船只。我踏上甲板,不觉转过头,刹那间,我被岸上的情景撼动了,岸边站满了前来送行的老百姓,他们默默地望着我们,许多人在轻声抽泣。有人在喊我,循声望去,见梁大娘一家站在岸边向我挥手,兔儿见到我,跨着跌跌撞撞的脚步跑到我面前,扬起粉红小脸看着我,伸手把一样东西放到我手心里。那是一个鸡蛋。兔儿说:“阿姨,早点回来呀!”听着他真切的童音,我心头一热,跨出船舷,抱起兔儿,我的脸与他的脸紧紧贴在一起,泪水止不住滚落下来。梁大娘和儿媳走过来,我扑上去与她们紧紧拥抱,大声哭泣。儿媳抿着嘴,低头把篮子里的鸡蛋往我口袋里装,连声说,“路上吃,路上吃。”大娘带着离别的不舍说:“记得回来看我伲,这里也是你的家哟。”我如鲠在喉,泣不成声,只能点头。这一别,不知何时能回来。当我返回船上时,船上岸上低旋着哭声和告别,船慢慢驶离了岸边,我挥着手,岸上的人们在我的泪眼和晨雾中渐渐消失。
我随部队北撤到了山东,姜齐已经升任旅长,我也担任了科主任。他始终关心着我,常常借口来医院找我,见不到我就坐立不安,似乎怕我跑了。他曾放出话,这辈子要娶我为妻。我知道,他喜欢上了我,这从他至今未婚就能说明。可我还是放不下江琦,我不相信江琦就这样离开我了,有时我在心里记恨起江琦,为什么一别四年杳无音讯,如果哪天江琦真的出现在我面前,我定要狠狠地锤他一番,以消解我心头因思念带来的怨恨,我的忍耐被磨砺得快消失了,我快要发疯了!
院长又来找我谈话,郑重其事地谈起我与姜旅长的婚姻,我以“不解放全中国不结婚”为由给挡了回去。院长不解地瞪我两眼,欷歔不已,甩着手悻悻地走了。
全国解放了,我们一路向北来到了大连。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来到江琦的家乡。我站在大海边,向南方遥望,大海无垠,浩渺而平静。我心呼喊:江琦,我到了你家乡,家乡已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回到了祖国人民的怀抱。你何时能回家乡啊!江琦,我想你!
20世纪50年代初,军队按照中央部署组建海军,我和姜齐都被调到大连海军工作,我在海军医院担任科主任,姜齐担任了海军基地副司令员。我们的婚事再次被组织上提及,院长已经升任军区卫生部长,他很严肃,很诚心,很真挚地与我做了一次长谈。“思雅主任”,他这样称呼我,“现在你的两次借口已经被完完全全地打破了,我们打走了日本鬼子,解放了全中国。俗话说:言不过三。你不要再有第三次借口了吧。”我默不作声,心里一时没了对策。看到我无语,他嘿嘿笑了,“你说说,姜副司令员有什么不好,他等你这么多年,就足以说明他的一片诚心了。我知道你心里还放不下江琦,这么多年杳无音讯,就已经说明问题了。你要现实一些,你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姜副司令员也30多岁了,难道你还要他继续等下去吗?再下去,你可就成实实在在的老姑娘了。我可是听到一些议论呀!作为你的领导,我是要对你负责任呐。况且,姜副司令员的名字叫上去与江琦同音,你就当是在叫江琦吧。俗话说,一笔难写两个秦字,那一声还能叫两个江琦呢。”他喝了一口茶,继续苦口婆心说,“你们都是经历了战争考验的同志,尤其是江副司令员,他的政治觉悟比你高,和他结婚,政治上会有提高。组织上早就看好你们这一对了。江副司令员对你也是一片真心,他是真心实意地喜欢你呀!”他说得口干舌燥,我听得心烦意乱。
夜晚静默后,我站在阳台前望着南方和满天星斗对梦中的江琦说:“对不起!我这个孤雁飞得太累了,想安个窝休息了。你别怪我,我只能这样了。”
一个金秋十月,我和姜齐结了婚。老院长,现在的卫生部长终于喜笑颜开了,他端起酒杯与姜齐一饮而尽。婚后,姜齐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他长我8岁,把我当小妹妹照顾。虽然工作繁忙,他也不忘每天清晨为我泡上一杯清茶,他晓得这是我在梁大娘家就已养成的习惯。他听我的劝告,戒掉了多年的抽烟习惯。当然,我们也有不相容的地方,我经常会因他的随地吐痰,不爱干净而懊恼生气。这时,他就会一边说“莫急,莫急”,一边赶紧打扫,还笑嘻嘻地请我去检查。娶到我,他心满意足,时常对人说:“别看我长得又黑又丑,我婆姨又白又净,可是个大美人嘞!”
我们一同去上海看望我的母亲。在见到我的一刹那,母亲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摘下军帽,靠近母亲,母亲看清了我,顿时老泪纵横。我扑到母亲怀里,像孩子似地大声嚎啕。母亲用手锤着我的肩膀,边哭边说:“雅儿,侬哪能一点音讯也不给我呀!我快想死你了。”母亲抬头,看到了我身旁站立的姜齐,止住哭,带着疑惑的眼光转向我,我把姜齐介绍给母亲。见到女婿,母亲用手绢擦了把泪,忙招呼姜齐坐下。她在我面前细细地观察了姜齐一会儿,会心地笑了。我想母亲对姜齐一定是认可了。当然啦,女儿嫁了副司令员丈夫,说出去,也感到脸上有光彩呀!
我们在苏州见到了陈老师的警卫员赵强,他已经是苏州驻军的团长。然后我们就去看赵强收养的陈老师的女儿。这孩子集陈老师和梅纹之优点,漂亮文静。赵强说:“这是抗日烈士的后代,要尽心尽力抚养,使她成为祖国栋梁之才,以告慰陈老师夫妇在天之灵。”
从江南回来后,我就怀孕了,可我还是不顾身体,一心扑在工作上,致使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了。过了两年,我又怀上了第二胎,不想是宫外孕,不得不做了手术。不想,手术后,医生告诉我,由于我两次身孕导致的身体状况,我今后不会再怀孕了。这让我万分痛心失望,没能给姜齐留下后代,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我心怀愧疚地看着站在病床旁的姜齐,泪水沿着脸颊无声地倾泻下来。姜齐伸过手,握紧我和蔼地说道:“婆姨,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可以一心一意地爱对方嘞,没有人来分我们的爱啰。最重要的是我们相爱就足够嘞!”他说得很轻松,对我还做出一个微笑。但我看出,他的微笑很勉强,是极力装出来的。他是在压抑痛苦来安慰我。
十年浩劫中,姜齐被打成走资派。他很不理解这种做法,对造反派说,我参加革命,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解放劳苦大众。现在,我反到成了走资派了,简直是没了黑白。他的这种抵触被认为是死不悔改,招致更狠的处理,我们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在那段经受磨难的日子里,姜齐重拾他断了多年的烟卷,而且抽得更多更狠,夜晚便开始咳嗽。“文革”结束后,我们回到了大连海军基地,姜齐恢复了副司令员职务。他拼命工作,想抢回被十年耽误的时间。我被调到海军疗养院担任了副院长,也是废寝忘食地工作,不久,我被任命为疗养院院长,直到我离休。
由于姜齐拼命地工作,加上他总也断不了抽烟,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我到处给他找药,带他去北京、上海大医院治疗,期望他的病能够好起来。糟糕的是,肺病不但没好,又发展成肺癌。他不停地咳嗽,尤其在夜间更为严重,弄得整夜睡不好,饭量也在减少,人消瘦得像一捆干柴。我整天守着他,在他的胸口不停地扶揉,以减少他的痛苦。终于有一天,他再也起不来了。他躺在医院病床上,瘦骨嶙峋,不停喘息。估计是知道了自己将久别人世,他拉着我的手,用手指轻轻滑动我手背,望着我,别离中的眼光没有半点虚假。他断断续续说:“感谢你陪伴了我一生!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有另一个江琦,别怪我从他身边抢走了你,我实在太爱你嘞,你是我的好婆姨。我走后,你去找他吧,回到你那个江琦的身边吧。”我感到胸口被堵住,扑到他身上,只叫了一声“老姜”,泪如雨下。
没有了姜齐,我重又成为孤雁,感到极度孤独。夜晚久久不能入睡,望着灰暗的天花板发呆。姜齐和江琦的音容在我面前轮番出现,渐渐地,江琦的形象越来越清晰。这么多年,他其实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我,始终潜藏在我心灵深处,令我魂牵梦绕。初恋的感情最真挚,最真实,最真切,一辈子忘不掉。姜齐走后三年的一个夜晚,我梦见江琦,他对我说:“思雅,知道我在哪里吗?我睡的地方太潮湿了。你能来看看我吗?”我忽地从梦中惊醒,仰身坐起,望着茫茫黑夜,似乎看到江琦在四明山向我招手。他在呼唤我,我不能等待!即刻决定来四明山。
说到这,秦思雅用纸巾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抬起头,向窗外的四明山眺望。孟桦起身为她的茶杯续上开水,青绿的茶叶在水的冲泡下翻滚飘卷,飘出一丝清香。孟桦的眼睛早已被泪水浸湿,她被秦思雅的真爱故事所打动,这位文静柔弱的老妇人竟能在抗日烽火中端起机枪射向侵略者。秦思雅在她面前变得高大丰满起来,令她敬佩不已,她决定帮助她寻找常江琦。
要想找到常江琦不是件易事,毕竟已经过去50多年了。但孟桦下了决心,不管怎样也要找。常江琦不仅是秦思雅的初恋未婚夫,也是抗日烈士,是祖国的功臣,一定要找到!
下班后,孟桦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让他自己解决晚饭问题。之后便径直去了父母家。父母是当地的居民,一定知道一些抗日时期新四军的事。饭桌上,孟桦问父亲知不知道抗日时发生在虎头山上的那场战斗。父亲叉开手指,来回撸捋粗短灰白的头发,反复念道:“虎头山,虎头山。”思索一会儿,抬起头,像发现了什么,说:“去问问魏老伯,抗日时,他就住在虎头山附近,常去虎头山砍柴,还在那里打过猎呐。”
魏老伯解放后就从山里搬到镇上居住了,如今70多岁,腰不弯,背不驼,就是记忆有些衰退。改革开放后,凭着一副硬身板,承包了十几亩鱼塘,靠勤劳致富,盖起了两层楼房。老了,年龄不饶人,他把鱼塘交给儿子饲养,与老伴过起舒坦日子。当孟桦领着秦思雅和助理员上门时,魏老伯的老伴魏阿婆正在院里嚷嚷:“老头子,让你去菜地摘点刀豆,你把长豇豆摘回来了,让你去菜场买点洋山芋,你却把山芋买回来了。你真是老糊涂了,一点记性也没有呐。”
一个老人坐在院里在修理鱼篓,鱼篓用山竹编织而成。老人面前地上摊放着一些细洁的如小手指宽长长竹片,他拿起一根竹片,把头部插进鱼篓破洞处,然后再前后缠绕编织,破洞处被补好。老人的手仍旧灵活,丝毫没有近80岁人的迟钝。听到老伴嚷嚷,他似乎已经习惯,只是低头笑笑,仍未停下修补鱼篓的手,直到孟桦招呼他时才抬起头。
孟桦向秦思雅热情地介绍魏老伯夫妇,就在魏老伯抬起头,对她微微一笑时,秦思雅明显看到了魏老伯额头上那一块深深的疤痕。她一怔,几分钟的思吋,一幅画面便在秦思雅脑海中呈现:50多年前那次去县城救治陈老师,莫不是他就是在城门口遇见的那个人?她走近魏老伯仔细地看,虽然过去50多年,老人脸上布满了皱纹,长满了老人斑,可是他的脸盘没有变,肩背还那样宽,脸色还那样红,看人的眼神似乎还是当年城门前的惊诧和疑虑。魏老伯似乎对面前的秦思雅也发现了什么,他眯起眼,仔细打量着面前这位虽陌生又似曾熟悉的妇人。
突然,魏老伯问到:“你是不是50多年前去过县城,我好像在县城门口见过你。” “去过”,秦思雅肯定回答,此时,她已经能确定魏老伯就是那个人,他额头上的伤疤留给她的记忆太深了。
一旁的人惊异起来,魏阿婆指着秦思雅,一脸狐疑问魏老伯:“你见过她?50多年前就见过啦?”
“见过,见过。一定是她。”魏老伯像是回答老伴,又像是自言自语。
孟桦感到有门路了,趁势问:“魏老伯,那你也记得50多年前发生在虎头山上的那次战斗啦?”
“记得,记得。那次战斗恐怕我这一生也忘不掉啦!”魏老伯说。
看到此情形,孟桦拉了拉魏阿婆的衣襟,魏阿婆像突然梦醒似地忙招呼大家进屋入座。
魏老伯提起那次战斗,就像打开了话匣:“50多年前,那天一早我走出家门去虎头山一带砍柴,刚走到离山崖不远处,突然,山上传来激烈的枪声,还有日本鬼子小钢炮的炮弹爆炸声。我急忙躲到一个岩石旁,探头往枪响的地方察看,炮弹剧烈的爆炸声,掀起灰尘、泥土、草坷垃向四处扩散开来。战斗看样子打得不小,整整打了一上午,直到后半天,枪声才零星稀落下来。我壮胆向虎头山猫着腰走去,看到不少鬼子从山上下来,还抬着不少受伤的鬼子。我想,这一定是新四军与鬼子又干了一仗。从战斗的持续时间和枪炮声的激烈程度来看,鬼子一定死伤不少,我心里暗暗高兴,‘小鬼子,该死!’
我沿着九曲河走到虎头峡处,这里是虎头山与另一山的峡谷,河水很急,还有小的漩涡。我站在峡谷河边一块不大的草地上,抬头查看虎头山,那是虎头山一侧陡直的峭壁,有几十米高。我在河边还能闻到浓烈的火药味。我看到峭壁的岩石有小块的脱落,长在峭壁上的草木也有松离和掉下的样子。我继续向虎头山峭壁一侧走去,突然,我看到了一个人侧身躺在峭壁下的河水旁,他的脚已经浸人了河水中。我四处看看,无声无息。我快速走到这个人身旁,把他扳将过来。他穿着新四军军装,大约20多岁,白净皮肤,瘦瘦的,胸部、肩膀、大腿还有胳膊都被子弹打中,鲜血把身体都染红了。我试试他的口鼻,已经没有了气息,身体已凉,开始僵硬了。当时我就明白了,他一定是在战斗中被鬼子击中,从虎头山一侧悬崖上跌下牺牲的新四军。我一阵心酸,眼睛不觉湿了,泪也流了下来。我赶忙拔了一些芦苇和蒿草盖在他的身上,把他先掩护起来。我奔回家,拿了一大块家里贮备的干净白布。我回到虎头山峡谷边,在一块空地上挖了一个深坑,抱过那位牺牲的新四军,从他的口袋中翻出一张照片,那是一张他和一个年轻女子的两人合影,我估计,那女子可能是他的媳妇吧。我用白布仔细地把他前后上下包裹好,放进墓坑中掩埋好。我记住了墓地,就在靠近峭壁旁的河边,旁边有一块凸出的大石头。”
孟桦问,“当时怎么没有告诉新四军?那照片呢,为什么没有拿出来呢?”
魏老伯喝了口茶,叹了一声,说:“这仗打完后,新四军部队就转移了。我把这张照片精心地收藏好,心想,总有一天,打走鬼子时,我再拿出来交给新四军首长,他是为抗日牺牲的新四军烈士,我要保护好他的遗物。可是,打走了鬼子,新四军也很快撤离了四明山区。解放后,又是三反五反,四清,又是文革,我看到那么多新四军,老干部被打倒,我就吓怕了,不敢拿出来,怕伤着牺牲的新四军,那我就对不起他家人了。”
孟桦听到这,果敢说:“我就是代表组织为这事来的,现在你可放心拿出来了。”魏老伯眼睛一亮,踩着踏实的脚步转身上楼,不一会儿,他把一个小木盒摆到桌上。木盒外的红漆已斑驳脱落,看来年头很长了。他打开木盒,拿出一个用白手绢包裹的小包,层层轻轻掀开,里面豁然显出一张很旧的黑白照片。
半个多世纪的尘封瞬间被揭开。映入眼帘的正是那张秦思雅与常江琦在上海离别时的合影,秦思雅颤抖着双手捧起这张照片,拿出那张她珍藏的合影,两张照片一模一样。秦思雅只叫了一声“江琦”,便扑倒在桌上,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魏阿婆抚摸着秦思雅,安慰道:“找到就好,找到就好。”转头对魏老伯说:“老头子,5分钟前的事你忘得干干净净,50年前的事你到记得清清楚楚。看来你还没有老糊涂啦!”
虎头山下峭壁旁的河滩上,常江琦的遗骸被挖掘出来。秦思雅双膝俯卧在墓坑旁潸然泪下,她含泪捧起常江琦的遗骨,轻声地、爱怜地说道:“江琦,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泪珠滴落,浸湿了这片梦魇的土地。四周寂静,只有风裹挟着丝丝凄婉的悲痛在人们心头掠过,在芦苇蒿草中发出沙沙声响,大地为之扼腕叹息。
当地人民政府在桃花岭陈老师梅纹夫妇墓旁为常江琦建了一座新墓,墓碑上镌刻着“常江琦烈士之墓”几个大字,凝重而肃穆。每年清明时节,秦思雅都要在绵绵细雨中来桃花岭祭奠常江琦和陈老师夫妇。她每回都用手巾清洗墓碑,还采来映山红、贝母花和小黄花放在墓前。
孟桦又陪同秦思雅去桃花岭看望了梁大娘一家,可惜,梁大娘已经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去世。好在梁家媳妇不仅用瘦弱的身躯支撑起这个家,还把儿子兔儿培养成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兔儿上了高中,毕业后回乡,经历改革开放的浪潮锻炼,现在已经是卓有成效的企业家了。看到秦医生的重访,全家人悲喜交加,热泪相拥。
秦思雅已经三年没在清明时节来桃花岭扫墓了,这让已经升任镇长的孟桦担心起来。上班后,她想给秦思雅打个电话。这时秘书进来递给她一封信。信封上熟悉的字迹让她立即想到了秦思雅。她赶忙拆开信,果然是秦思雅来的。
孟桦您好:
久未联系,甚念!由于身体原因,我已三年未能来桃花岭扫墓了,为此我身心焦虑,盼望您能在清明时节帮我看望烈士们,为他们,也为我扫墓。我的故事您已知晓,这一生,我始终爱着常江琦,爱着四明山,那是我们齐心协力打走鬼子的地方。那是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令我爱恋而不能舍弃的地方。我的日子不多了,我有一个请求:在我离世后,请将我的骨灰安放在常江琦烈士墓旁,我生不能与他同行,逝后也要与他同在一起。
寄去我的储蓄20万元,作为我建墓和祭奠江琦、陈老师梅纹夫妇的费用,余下的费用用于希望小学的建设。
拜托了。谢谢!
秦思雅 2005年2月
孟桦此时眼中已经溢出了泪。望着窗外横亘起伏的四明山,心里默默念着:“放心吧,我一定会办好的,你们是为抗日而来的四明山,为四明山百姓打鬼子,为国家捐躯。我作为四明山的后代责无旁贷。”
2006年,秦思雅去世了,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常江琦的墓旁,这对抗日情侣终于在桃花岭上相聚长眠。
办理好秦思雅的后事,孟桦伫立在松柏苍劲的墓碑前,放眼望去,雨后的四明山巍峨碧绿,湖水泛起层层涟漪,阳光照射下,大地更显落英缤纷,绚丽富饶。清代龚自珍的诗篇在脑海中响起: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2016.1
上半部分:请查阅:http://www.shwyw.com/portal.php?mod=view&aid=1026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属作者所有,如有需要,请与作者本人联系,或者与上海文艺网编辑部联系。

扫一扫上 海文艺网

扫一扫 上海文艺网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