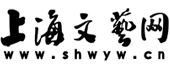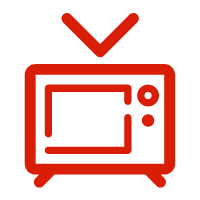现在我常常陷入回忆。
在回忆里,有一个场景时常在脑海里泛起。二十八年前,在初春的一个晚上,我与家人坐着一辆大卡车回到了故乡。此时,春天虽然已经到了,但空气中仍带有丝丝寒意。
说是故乡,其实是父母的故乡。不过,做为从农村走出的他(她)们而言,这个故乡是广义的,因为我们所回到的只是行政区域中的县城。真正的故乡,还是在那有山、有水的农村。
就故乡而言,它其实活在记忆里。这种记忆的深度决定了故乡在某个具体人中的份量。而做为一个八岁多的孩子,我对于故乡的记忆是模糊的。我知道,我生在农村,在生我的那一年,川东北大旱,粮食绝收,虽然夏收刚过,但家里没有余粮,母亲没有奶水,这种饥饿的感觉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除此之外,关于这块土地,我就没有多少记忆了。因为父亲在外服役的缘故,我在三岁多时就离开了这里到部队去。父亲做为一名毛泽东时代培育出来的模范军人,在铁道兵部队里服役,曾经有老长一段时间,哪里有铁路哪里就是我的家。后来,直到父亲所在部队把铁路修到了湖北均县武当山脚下时,我们一家人才在一个军队家属的安置点上安定了下来。这是个离乡场还有些远的小山村,我们住在一个相对平坦的小山梁上,房子则是清一色用“油毛毡”搭建的简易棚屋。这种房子的好处就是夏天热冬天冷。我家分得了两间,一间母亲和两个姐姐住,一间分成了两半,用篱笆隔着,一半做为吃饭的地方,一半则只能摆下一张部队里发的小行军床,权当我的卧室了。妈妈在屋前用砖彻了个小灶,挨着墙码了不少木柴,再用篱笆把房前围了起来,安了个谁都能够用手打开的小门,便就是家了。而父亲,依然一年里难得见上他几回。因为,他所在的部队又开进到了山东曲阜,即孔仲尼的家乡,修筑兖石铁路(兖州到石臼所,石臼所在山东日照)。在我五岁多那年,母亲把我交给了一个由年轻士兵组成的部队运输车队,让我独自一人去见见父亲。从湖北到山东,路途遥远,车队走走停停开了近半个月后,终于在一个部队大院里见着了父亲。我的到来使父亲很高兴,部队出操、野营拉练、开会时,他都带着我去。闲暇时,常带着我满城乱逛。他有一辆自行车,便让我坐在前面,游遍了孔府、孔庙、孔林。我至今仍记得,我和父亲去游周公庙时,时逢该庙正在修缮,那正庙中供奉着周公像并未完工而用红布搭着头部,所以不对外开放故只得怏怏而去。后来,我和母亲及两个姐姐又去了曲阜几次。
不过,湖北均县始终是我的家乡。大姐一路读书,小学毕业时还考上了当地的重点中学;而我,一晃也成了一个八岁孩童,就在当地的一所小学校里读着书。学校距离家很远,要走近一个小时,而且要穿越几座大山;其中有座山很阴,一天中见着阳光的时候不多,且在必经之路的山梁上能见着许多坟墓。但在当时,这并不算什么,我就天天这么走着。不过,即使在白天,我一个人还是不敢走,得跟着院里的其它小伙伴们一块走。学校旁有一条水渠,水清且足,夏天时我总爱赤着足走在水渠里;还学会了叠纸船,往水渠里放,看它漂得老远,其乐融融。而且,也和不少小伙伴成了朋友。平日里我喜欢跟着他们捏泥人、滚铁环玩。记得有一年冬季奇冷,早晨起来后发现,大雪居然把家门前的篱笆给压塌了。这是我记忆中最大的一场雪、最冷的一个冬天。至今我的左手上还留着一块白色的疤痕,正是那个冬天生了冻疮后留下的。妈妈用从部队里找来的柴油将木柴浸过后生火给我煮了早饭吃,在将我的手上冻疮冰口处涂上“凡士林”后,给我戴上风雪帽和手套,便让我上学了。不过,在我而言,倒是兴致勃勃。我顶着风雪,一会儿便转过了山头,脱了母亲的视线;见离上课还有一段时间,便脱下母亲给我笼着的这全套“装备”,跟着小伙伴们在雪里撒野,顾不得手上长满了冻疮,赤着手就生吃雪、捏雪团、打雪仗、堆雪人;嘿,玩得那叫痛快哟……
正当我已“反认他乡是故乡”时,父亲从部队转业了,于是在外边晃悠了这么几年后我又回到了故乡。但在这外边的几年,恰恰是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所以,关于“故乡”,一直对我是一个可疑的概念。而且,我也没有想到,从此,我便开始在了这座小城中的生长、生活--直到现在,一晃快三十年了。
在二十八年前的那个晚上,我在家人的搀扶下跳下大卡车,便见着了这座坐落在山脚下的小城。空气格外的明澈,能见度非常之高,天上的星星很多,而且距离山、距离城、距离人都显得那么近,说“手可摘星辰”,倒并不夸张;在一条小河的边上便是所谓的“城”了,人户中透着的电灯光也如繁星点点,把人、城、山、水、星全部都囊括了在内。
现在,许多的事情都忘却了,但这一幕,却深深铭记在了我的脑海里。在将近三十年前,南江是个多么美丽的小山城啊!所谓“千秋家国梦”,亦不过如此。
现在,尽管我已对这座城市到了连空气都熟悉的程度;但是,我在心里知道,在二十八前的那个晚上的空气和感觉,我是再也找不到了。然而,我还要在这里生长着,目睹着,思考着,平静着,沉默着。
当在一个人的思维里,故乡做为一种意象频繁出现时,往往意味着这个人衰老了。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故乡是出生之地,“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走了这么一大圈后,终归要回到原点上去。这个时候,许多事情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种心态,原是经历过许多波澜诡谲、惊涛骇浪和恩怨江湖的人才会有的。我曾见过许多文坛的大家及小家们写的文章,故乡都是他们绕不开的话题,而且越是年老的,思之甚切,念之愈笃,归之更急。或许,他们疲惫了,累了,倦了。此时,故乡那时的许多记忆才浮了上来,让他们觉得只有在那个地方他们才活着比较真实,才说得是人话,做得是和泥巴一样实在的事。而在其它地方,就不好说了……所谓归心,便是烈士暮年,便是黄昏夕阳,便是“复得返自然”。但那大都是些老人了,可到了自己这儿,竟然也显得自然而然。那么痛切与悲悯,其实就和无动于衷一样,只剩下了属于自己的无病呻吟。所以,我之心态,也不过是个小人物的悲哀;人总是现实的动物,在心理需要补偿的时候,总是距离他最远的东西才最能让他解脱;而正是这种思乡心态,更折射出一个人的彷徨反复与九曲回肠般的私密空间。那么,穿行在这座被拆迁得面目全非的城市里,何处是我的故乡呢?
还是再摘一段话吧:“家乡是好难的事情,大家看到唐朝人写诗,几乎有一半都是‘天上明月光,疑时地上霜’,都是思故乡的,因为故乡对他们太遥远了,太难得了,为什么我现在说李敖我不还乡呢。我这次回来不是怀乡,没有乡愁,不是近乡没有情怯,不是还乡没有衣襟,没有眼泪,为什么我要这样,因为时代不该有乡愁……”(李敖先生2005年9月21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
而回过头来,关于乡土,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过自己的看法:“当前我们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在与传统伦理的接轨方面存在着巨大缺陷,说‘礼崩乐坏’,并不为过。……由于无法守住乡土,也就无法守住历史。”
所以,关于故乡,再说已是多余。
作者介绍:黄政钢同志(曾用名黄勇刚),男,汉族,现年39岁,四川省南江县人,现系巴中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自幼喜欢文学,现已在多家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已出版长篇小说《政工干部》、《我的快乐地下生活》;随笔集《城市行者笔记》、《政钢有思》。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公安文联文学艺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巴中市作家协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本文入选2015年中国散文佳作精选集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主编:毕凌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