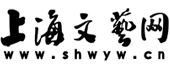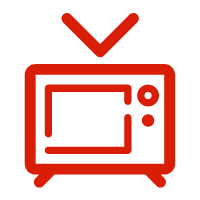靠水吃水。我家住在灌河边,父亲靠打鱼(捕鱼)养活了一家人。
同样是打鱼,七队的杨太军用的是丝网子——县城渔具店里随便都能买得到的那种——和一张小木船;河西张放鹰爷几个用的是几条老鹰船和几只鱼鹰(鸬鹚);本队杨怀中用的是一把铁叉,铁匠铺打出来的那种——杨怀中只捉王八。而我父亲的打鱼工具是旋网——长长的网缰绳,用力甩出,能甩到七八丈远。
从记事起,就知道父亲有两张网,眼小的稠网,用来打小鱼;眼大的稀网,用来打大鱼。初春河水转暖,父亲就开始早出晚归在灌河里打鱼,一入冬,父亲就在家里织网。织网这活需要耐心,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小时,偶尔趁父亲上厕所功夫,我会拿起他的网针织几下,父亲看见了,会说上一句“别学这个,成天泡在水里,老了没有好身子”,或者“打鱼不是好差事,鸡不叫狗不咬就要起来”-------但大多时间他选择沉默,就像他从没在孩子们面前说过苦和累一样。
织网很难,难在“生眼”。旋网是越织越宽阔,每织一圈,下一圈就要多出半个或者一个眼。土地下户后,搞副业的人多了起来,有人看父亲打鱼有些经济来源,就自己买了纤维和尼龙线,削了网针,像我父亲一样坐下去织网。织网是很花时间和精力的细活,我父亲能坐得住,那些人就不行了,三天一织就烦了,再加上不会“生眼”,很多人就选择了放弃。于是就有人提出买父亲的渔网。记得腰庄子的张建国,就挑了两笆斗大米给我家,把父亲的一盘刚织好的旋网欢喜地背回家。
父亲还会“篾匠活”。
入冬不能下河打鱼了,父亲就拿了蔑刀,去到五队的竹园。父亲专挑五年以上的竹子砍几十根,过称,付钱,然后扛回来。有一次父亲让我和他一起去竹园帮他抬竹棍,我问他为什么只选五到七年的竹棍,他说那些看上去很粗很鲜嫩的竹棍还有长(zhang)头,早早地砍了很可惜。
父亲先把一根竹棍分成两截,再一截一截地剖开,再一片一片地剖成数个小片。剖完之后,再一个小片一个小片地把篾青和篾黄分离。父亲分离篾青和篾黄时,沉重的蔑刀在他的手里轻快地移动,分离出来的篾青和篾黄细如丝、薄如纸,没有一根折断的。尽管他的双手粗黑,布满裂痕,但那却不是蔑刀和篾子划破的。父亲每次剖篾子,家门口都飘满竹子的清香。
父亲用剖好的篾子,编织成灶上用的筲箕、过年盛放圆子和酥鱼酥肉的“气死猫”以及粪箕子等。母亲把编好的物品挑到集上,很快就会卖完。
父亲还编灯笼,就用竹篾子,每年的正月十五都编。
父亲编灯笼,全用结实的篾青子。篾青子要提前几天剖好,然后放在池塘里浸泡两天,父亲说这样更耐用。篾青子剖的很细,父亲说这样灯笼会更亮堂。父亲把灯笼编的像一个精致的圆柱,上下通透,口口处篾子斜着交叉排列,密集而有花纹。编好的灯笼,使劲朝地上一扔,弹起很高却不会变形。
正月十五的上午,我们是最忙碌的。三姐打浆糊,我和五哥裁纸、糊灯笼。那时家穷,灯笼纸只能用很薄很便宜的“白河捻纸”。我们先把灯笼四周的篾子刷上浆糊,再小心翼翼地把“白河捻纸”粘上去,两头口口处再向内折叠、粘紧。每粘好一个灯笼,我们就小心翼翼地拿到很少有人走动的地方放置,等待浆糊晾干。
每每这个时候,母亲会把她塞在墙缝里、夏天染小鸡没用完的颜料抠出来。我找来小碗,把颜料倒进去加水搅拌几下。那时我们会在灯笼上画几片不草不树的叶子,再用或红或紫的颜料在绿叶间点一些点点,算是花朵了。有时也会写上几个字,譬如百花齐放。
父亲总是早早地锯好数块方形的木板——这是灯笼的底板。他会在每一块底板中间钉一根钉子,蜡烛就插在这根钉子上。底板上还要钻两个孔,一根稍粗的长篾子弯曲后,两端插在孔孔里,灯笼的提手就做成了。
早过十五晚过年。母亲总是这样说,也总是这样做的。远近还是起伏的鞭炮声,我们就把丰盛的“十五”过了。虽然天还大亮,我们还是迫不及待地拿出灯笼,插上蜡烛——但蜡烛不到天黑是不敢点上的,每晚只有一根小小细细的蜡烛,点完了,当晚就没有了。
父亲显然比孩子还要急,天一黑,他就把两个灯笼挂上堂屋大门外的钩子上,并且点燃了。有次我问:“这么早点着了,不怕洋蜡点完了?”他笑着说:“趁早点上,你大哥二哥马上要来俺家,天黑路不好走,给他们照照路!”那时大哥、二哥都早已成家分开过日子了,但每年正月十五各自吃过饭,都要来我家坐坐。
天终于暗下来了,赶紧点上红蜡烛。找一根麻秸或者一根小竹竿挑上灯笼,这样就不会烤到手。虽然家里的房子不大,按惯例还是要先“照照”。我跟在五哥和三姐身后,把灯笼伸到房间每一处偏僻的地方,边走边唱:
“照,照,照蝎子,蝎子死在墙裂子;照,照,照蜈蚣,蜈蚣死在当门子。”
房屋和当门子照一遍后,就提着灯笼出了门。依旧是冬天,哪怕已经打春,温度还是很低。但丝毫没有寒意。手是红的,别人的脸是红的,倘若地上有积雪,雪色也是红的。门前屋后也要照几圈,也是边走边照边唱。再转到门口时,父亲会问:“大路照了吗?大路照照,一年亮亮堂堂地走!”然后又排了队,朝一天不知要走多少趟的大路走去。路上,会汇合其他家的孩子,就在一起排了队,边走边照。远处,已是满地晃动的星光了。
灯笼要打(玩)三天,正月十七的晚上,是要“拼灯灯”的。
我们会在吃过晚饭后,提了灯笼,疯跑到灌河边,满庄的孩子越聚越多。我们把河滩的枯草、芭茅点着,再追逐、打闹,用自己的灯笼碰撞别人的灯笼,到处是叫声,到处是笑声,有的灯笼扁了,有的灯笼碎了,有的灯笼燃烧了,灌河,火一样地流淌。
记忆里一次最深刻的“拼灯灯”,应该是读小学四年级时。我们提着纸张破碎的灯笼欢喜地回到家,父亲笑着说:“就知道我儿子的灯灯不会烂!”我大声地描绘别人的灯笼碎成什么什么样,父亲听后说:“人家的灯灯都是篾黄编的,俺家的灯灯是篾青子编的——骨子硬!”
很难得看到父亲这样笑这样自豪。父亲因为成分不好,大集体时经常被批斗,听说母亲还自杀过,我的二大爷(父亲的二哥)就是没有坚持下去,上吊自杀了。父亲一直让几个孩子读书,他说读书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读初中时,和曾经批斗我父亲的那个人的儿子玩得比较要好,父母就反复劝说,要我远离他。见根本就说服不了我,有一次父亲咬着牙、青着脸对我说:“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师婆跳假神”,母亲也说:“人牵不走,鬼牵乱转。”直到参加工作,有一次我参观一个地主庄园,看到地主剥削欺压长工、地主儿子打骂长工儿子的描写,立刻想到父亲曾经讲述的过去。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和那个人的儿子来往了。五年前的一个清明节回去给父母上坟,在三姐家里吃饭时,五哥讲述他如何如何好吃好住地款待那户人家的儿子,我当时就想:如果父母知道了,该是多么地悲哀。
今天又是正月十五,夜不能寐,仿佛又和父母哥姐聚在那几间土坯房里一起糊灯笼一起过节,仿佛又看到父亲在黑夜里把他的红灯笼高高地挂上大门口,又听到他说:“天黑路滑,让孩子们都能看到来家的路”、“我家的灯灯都是篾青子编的,骨子硬”……
己亥正月十五凌晨嘉陵江畔
作者简介:余昨非,原名余超,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河南固始人,现居四川。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在线签约作家。